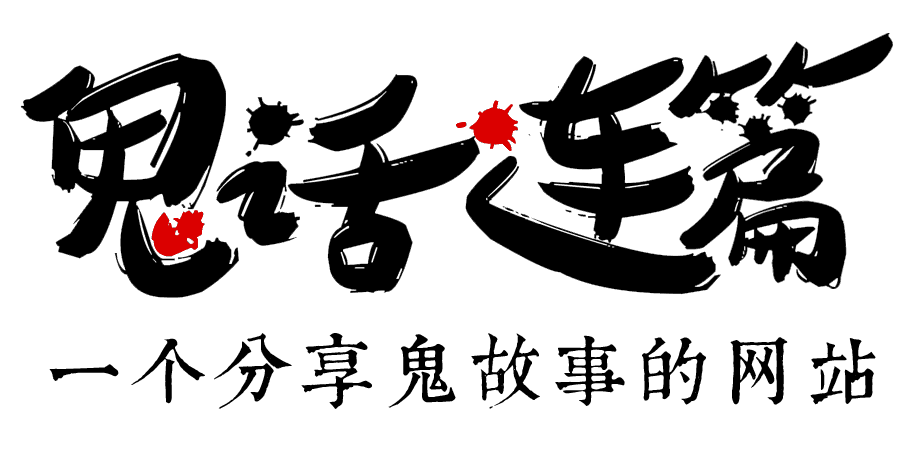我们在研究这些案件之间的共同主题以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它们缠绕着我们的时候,肯定会想到“原型”这个词。从潜伏的恶魔到家庭的内幕,从成名及其带来的种种后果到不可思议的神秘性,从性强迫到无辜者的堕落,这些案件中的任何一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都代表了一种我们能够理解的原型。这些案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代表了某种强大东西的黑暗一面。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如此令人着迷的原因了。
但是它们也确实很重要,而且具有启发意义。因为除了给我们一个了解人的本性的窗口之外,它们还向我们表明,当我们没有准备好来应付它们时,到底会发生什么后果。
每个案件的侦破都极度困难,都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和不规范。在白教堂连环谋杀案中,侦查人员根本不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凶手。在丽兹·伯登案中,他们被社会上对妇女阶层的俗套看法束缚了手脚。在林德伯格绑架案中,善意的、富有同情心的警官们失去了对案件调查的控制权,致使指向绑架者的线索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了。在克里斯廷·舒尔茨和琼贝妮特·拉姆齐谋杀案中,犯罪现场和证据都被一时的冲动行为破坏了,侦查行动也因警察部门的工作程序有问题而备受阻碍。在波士顿勒人魔连环谋杀案中,其中一个人的坦白倒是使案件有了一种简单的、快速的“解决”,但是最终证明此种解决是不令人满意也不令人信服的。
同时,这些案件也是刑事侦查和刑事司法中更大问题的体现。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的有几件事情。
在这本书横跨的一个多世纪中,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认为如果这些案件发生在今天的话,是可以帮助警方侦破其中一些的。我们有不论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都没有的技术、能力和知识。DNA分析、医学检查、计算机、证据保全、激光增强技术、现代心理学、行为分析、审问技巧、威胁分析以及其他基本侦查技术,这只不过是我们现在拥有的资源中的一些而已。然而,正当你读着这本书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停尸房中正躺着成千上万名身份尚未确认的已经死去的被害人。1960年,谋杀案侦破率大约达到了91%。现在,由于诸如“陌生人”谋杀案的增加(凶手和被害人之间互不相识),侦破率大约只有65%。
除非我们真正利用所有的东西,并且学习如何去一贯地以协调而正确的方式展开侦查工作,以上所有这些现代取得的发展和改进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有非常先进的毛发和纤维分析技术,但是却在调查取证人员到来之前破坏了现场,那么你就会一无所获。如果你可以从子弹上的划痕来确定哪支枪是凶器,但是却无法确定那把枪案发时在谁的手上,你也将一无所获。如果DNA证据可以确定整个世界中哪个具体的人当时是在犯罪现场,但是你的证据保全过程出了问题,那么你同样将一无所获。我们可以如此这般罗列出无数例子。
我在全国讲授犯罪学和相关学科。当我与被害人的家人们进行交谈时,人们总是向我描述一些我闻所未闻的极端可怖的犯罪案件。而如果我都没有听说过的话,那么除了那些受犯罪影响的人之外,还有什么人会听说过这些案件呢?在像约翰·维因·盖西、杰夫雷·达摩尔和约耳·里夫金等这样的连环杀人犯不断作恶之下,甚至在当局知道发生了问题之前,就已经尸横遍野了。现在不仅比以前有更多的暴力犯罪,而且这些犯罪越来越多的是由“陌生人”干的:他们并不认识被害人,而且以前也和被害人没有发生过什么过节……被害人之所以被害几乎纯属运气不佳。此种谋杀案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难题。
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手头现有的资源,比我们现在更加高效、更加好地利用它们。
1985年,我参加了在匡迪格市举行的联邦调查局的“暴力犯罪打击计划(VICAP)”成立剪彩仪式。司法部长威廉·弗伦奇·史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也参加了。“暴力犯罪打击计划”是一个电脑数据库,里面列举了暴力犯罪的各种详细细节。这个数据库的用处是,当全国超过一点七万个执法机构中的任何之一要对某宗暴力犯罪(比如很可能是连环杀人或连环强奸案的某个案件)展开调查时,警方就可以通过填写一份详细的计算机问卷,将这个案件输入到计算机中。接下来“暴力犯罪打击计划”就可以提供给警方全国范围内与当前案件类似的证据或线索的任何其他罪犯的信息。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主意,最初是由洛杉矶警察局谋杀案警探皮尔思·布鲁克斯提出来的。
在犯罪侧写计划马上就位并发展得不错的同时,“暴力犯罪打击计划”却停滞下来了。当我在1995年从联邦调查局退休的时候,这个数据库中大约只输入了几千个案件。各个地方侦查机构都嫌麻烦,特别是当其他许多机构都不积极的时候。但就在同时,加拿大却研究了我们的系统,随后建立了自己的系统,并开始运作。有什么区别吗?加拿大警方被强制命令参与其中。不使用这个系统的任何机构都可能面临着失去政府拨款的风险。除非每个人都参加,否则建立这样一个复杂的全国资源库是毫无意义的。
任何读过马克的著作和我最近发表的小说《折断的翅膀》的读者都知道,长久以来我都一直提倡建立一个“警察紧急行动队”。它由刑事侦查所有领域中的专家构成,包括警探、犯罪侧写师、验尸人员、犯罪现场专家、弹道专家、毛发及昆虫专家、法医专家、纤维和血迹专家以及有必要包括的任何其他方面的专家。他们将乘坐设备良好的飞机出现在全国各地的犯罪现场,在犯罪现场还完好无损的时候就开始案件的侦破工作。他们不一定非得都是联邦调查局的成员。我认为这个紧急行动队就应当像军队里面的“三角洲部队”一样,可以从任何机构中抽调最能干的人加入进来。
我还提倡建立一个独立的全国实验室来处理证据,整个实验室要独立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联邦机构。在这个实验室工作的人员都必须是最优秀的,他们的报告应当是可靠的、无可非议的。让我们棘手不堪的这些案件中的许多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证词或证据。例如,标记为十六的那根横档,到底是取自林德伯格绑架案中罪犯用的那架木梯,还是被急于破案的警员拿了别的木头来冒充?伊丽莎白·肖特是在活着的时候还是死了之后被罪犯切成两截的?这个实验室对确立刑事侦查和刑事指控中证据的可信性大有帮助。
同时,各州也可以有所作为。许多情况下,地方警察局或者检察官办公室的主要问题是,它们无法或者不愿意与被害人、公众以及其他部门沟通。我认为,如果每个州都设立自己的重大犯罪特别工作组的话,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极大的缓解。某些州已经这样做了,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
特别工作组应当和各地警察局及治安办公室的代表、州侦查人员和实验室人员举行定期会议。他们可以听取法医学各个方面的正式汇报,并且讨论热点案件和疑难案件。应当注意的关键一点是,州内任何地方的任何警官、警探或侦查人员都应当知道哪里有资源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资源。这会避免再出现拉姆齐案中的那种情形,因为当地方警察局没有必要资源或者经验时,它们能迅速调用最好的支援手段和信心(后一点更为重要)。
尽管联邦调查局在“暴力犯罪打击计划”上没有获得我所期望获得的那种成功,但是“全国警务研究院”却通过它的计划作出了无可估价的贡献。在“全国警务研究院”的计划中,警长、部门领导、高级警官和地方及地区执法机构的警探们,都来到匡迪格市接受深入的培训和指导,这使得他们能够熟悉执法行动的最新发展和最新技术。“全国警务研究院”不仅让它的毕业生获得了一种更深的理解以及更为广阔的视角,而且它还创造了一个由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人们组成的非正式网络,他们彼此相识,当有需要时他们会相互请求支援。
我获得的最大成功就是因为请求我所在部门支援的地方警官曾经在“全国警务研究院”学习过,并和我们逐步熟悉了。我在前一章中隐含地提到的对1985年在南卡罗来纳州发生的夏里·非·史密斯和德伯拉·梅·黑尔米克谋杀案的侦查,就是犯罪侧写师及其相关机构与优秀的地方警官结合在一起所能带来的优势的绝佳例证之一:我们在罪犯进一步作恶之前就将他一举抓获了。我经常说,我们之所以成功的两个关键理由之一是,负责案件的两个警官是非常优秀的。他们是警长吉姆·梅茨和副警长卢·麦卡提,都是“全国警务研究院”的毕业生。梅茨很清楚,请我们支援并不表示他的无能或没有把握,而恰恰是显示了他的力量和忠诚:他组成了最好的破案队伍来保护他所在的社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麦卡提、罗切斯特警长、林德·约翰逊以及许多像他们这样的警官,在我的书中总是英雄模范和榜样。
我写这些案件,还希望能够向读者说明其他一些教训和常见问题。
丽兹·伯登、劳丽·本姆本尼克和琼贝妮特·拉姆齐三个案件表明,一个人并不是在一天早上醒来之后就突然决定做个罪犯的,总是会有某些预兆性的行为。如果没有或者你没有发现,那么你就必须怀疑嫌疑人是不是确实是真凶了。波士顿勒人魔连环案件表明,罪犯是不会突然之间毫无理由地改变他的个性的。开膛手杰克、黄道十二宫、大丽花和拉姆齐案件都告诉我们,几乎没有所谓的无动机犯罪,只不过是我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罪犯的动机罢了。
林德伯格案、伯登案和拉姆齐案,特别是拉姆齐案,告诫我们,在不知道或不理解关键事实的情况下作出草率的结论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的结论往往是出于各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我们草率地作出结论,我们就正中各种花边小报和追求轰动效果的媒体的下怀了,我们也就和它们毫无分别了。在拉姆齐案中,即使是主流媒体也通过它们的影响力对所有人带来了损害……只有那个逍遥法外的罪犯毫发无损。如果让狂热占据我们的大脑的话,真相就可能被牺牲了,正如我们在亚特兰大奥林匹克公园爆炸案中所看到的,公园保安理查德·朱维尔遭到了不公指控。这个案件绝妙地说明了那些根本不懂得行为分析的人是如何曲解行为分析的。
传统智慧往往是建立在神话之上的,并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会有一套不同的标准。
丽兹·伯登不可能杀死她的父母,因为富裕有教养的女士是不可能做出此种行为的。
一定是某个像布鲁诺·霍普特曼那样的人杀死了林德伯格的孩子,因为真正的美国人是不会做此种事情的。
肯定是班比·本姆本尼克杀死了克里斯廷·舒尔茨,因为她是一个盛气凌人、诡计多端的第二任妻子。
拉姆齐夫妇必须为他们女儿的死负责,否则他们不会拒绝与警方合作。
这些都不是有关事实或真相的表述,而只是一种传统智慧的神话。
最后,我认为这些案件就像战争纪念碑上的雕像一样:上面只有几个具体的形象,代表着成千上万个同样作出无私奉献、承受巨大牺牲的无名战士。
琼贝妮特·拉姆齐被杀害之后两个星期,一名九岁的女孩(为保护她的隐私和身份,我们姑且称之为女孩X)被罪犯痛打、强奸、下毒,之后被扔在芝加哥声名狼藉的“卡布里尼·格林”公共住房计划项目的走廊里面,任其死亡。是一个看门人发现她的,当时她的T恤衫被勒在脖子上,身上画着匪徒的象征符号。她不是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她也并非来自一个显赫或富裕的家庭,但是她遭受了无言的痛苦。和任何被害人一样,她和她的家人不仅值得我们同情,而且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对罪犯表达愤慨。
根据联邦调查局1996年的《统一犯罪报告》,琼贝妮特死的同一年,在全美国,有八百零四名十二岁及十二岁以下的儿童被杀死。而我们只不过知道其中一个儿童的名字罢了。我并不是说琼贝妮特没有遭受罪大恶极的罪行,我只想说所有其他的孩子也应当得到同等的同情和关爱。
就像对待成千上万英勇倒下的士兵一样,你根本没有听说过的成千上万宗案件,从来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人们也从未分配充分的资源来侦破这些案件。这些案件同样令我极度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