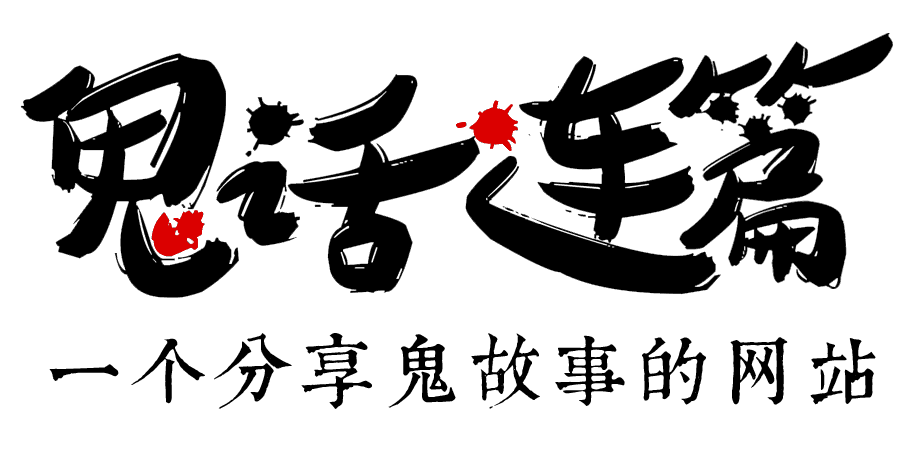1月10日,星期五上午,由布赖恩·摩根陪同,我在警察局总部见了史蒂夫·托马斯和托马斯·楚吉洛两位警探。他们都穿戴整齐干净,看起来有二十八九岁或三十出头的样子。他们在自我介绍时都很诚恳。我们去了一间有一个桌子、四把椅子的审讯室。
摩根规定了一些规则,就是我要回答关于拉姆齐夫妇的细节问题,以及我要谈谈我所做的事情、我的方法以及我的印象。警探们说他们没有意见。他们问我们身上是不是带了录音设备,我们说没有。
为保留记录之用,他们问了我的全名、出生日期和时间、家庭住址和电话等。我说我生在布鲁克林时,他们中的一位说能够听出我的一点口音。我用十五分钟描述了我的背景和经历,他们两个都说我很厉害。摩根加了一句:“约翰在这一行里最厉害,所以你们应该听一听他的意见。”他的话让我有些尴尬,但是我没有多说。
我向他们讲了我的分析,以及我相信拉姆齐夫妇的原因。托马斯和楚吉洛的身体语言表明他们对我所讲的很感兴趣。我说我相信罪犯作案的动机是出于个人原因,是针对拉姆齐先生的。我想十一万八千美元这个数字一定有意义,因为这几乎等于他从公司拿的奖金(十一万八千一百一十七点五美元)。这笔钱是通过电子汇款存入他的退休金账户的。他全年的支票余额应该就是那个数额。尽管我不很确定,但我感觉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
我告诉他们我的观点是勒索信的作者是一个白人男性,三四十岁,有些商业背景。(我仔细研究勒索信以后,把估计年龄减小了一些。在犯罪侦查分析中,年龄是最难确定的因素,因为实际年龄和行为年龄并不总是一样的。)
我说信的风格像商业信函,在一些地方勒索者没能够完全隐藏自己。他们问这个案子是不是由一个人单独干的。我说我认为是,并且这个人肯定是被人有意或无意告知了拉姆齐的奖金数额。如果是无意的,那么这个人可能在约翰·拉姆齐办公室的桌子上或者在他家里的桌子、茶几或者梳妆台上看到过支票存根或者打印出来的退休金计划。
犯罪本身和犯罪现场既有有条理的一面,也有无条理的一面,这表明罪犯并不老练。但是,即便他是一个老练的罪犯,他也要有很大的胆量才敢在父母在家的时候闯进家里杀死孩子。即使勒索信本身也表现出了无条理的一面。这封勒索信很长,里面有很多不相关的内容,所以要事先有计划才能写好。另一方面,纸和书写工具是从房子里面拿的,这表明他或者没有计划,或者非常非常地有计划——只使用房子里面的东西,这样不会留下其他线索。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罪犯一定是知道拉姆齐家人会出去很长时间,这样他才有时间写完这封勒索信。
我说不管凶手是家庭成员还是外人,我都认为勒索信不可能是在犯罪以后才写的,而肯定是在杀人之前就写好了。在我的全部职业生涯里,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么有控制力、思维这么清楚,能在杀人以后写出这么长、这么复杂的信。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我没有找到拉姆齐夫妇有什么杀死他们自己孩子的原因或者动机。从我得到的资料看,琼贝妮特对拉姆齐夫人来讲就是一切。在已经死了一个女儿以后,拉姆齐先生会更加呵护女儿琼贝妮特。
我必须说,不管这两位警探在这之后说了些什么,我觉得他们在当时都非常注意我所说的内容,并慎重地考虑了我的分析。我说,要抓住罪犯,警方和检察官办公室的公开声明一定要非常自信。我一步一步地和他们讲了我以前用过的手段。行为分析本身不一定那么有价值,但是有效的办法是要得到媒体的合作,让媒体公开罪犯的犯罪前后行为特征,这样罪犯身边的人就会认出罪犯。这应该尽快做,以免时间长人们会忘记。
“让我们看一看大学航空炸弹怪客这个案件,”我说,“大学航空炸弹怪客的露馅开始于他写信寄给了外界。因为我们有了用以评测的材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动机。”并且我们现在有机会把他写的东西公之于众,希望有人能够认出他的笔迹并报告给警方。我认为,如果“宣言”没有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那么西奥多·卡辛斯基可能还是住在蒙大拿州的小木屋里对全国进行恐吓呢。
可以马上得到结果的一个方法就是使用报纸和广告牌公开勒索信。1989年,特别密探加纳·门罗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为我的小组处理过一个案件。在那个案件中,到坦帕市访问的一个女人和她的两个女儿被人杀死了,尸体被扔在坦帕湾里。她们明显是性谋杀的受害者。唯一可见的证据是在这个女人汽车里找到的一张乱写的字条,上面写着从她的旅馆到找到汽车地点的路线。当其他线索没有结果的时候,加纳让当地警察局放大了这个字条,然后把它登在当地的广告牌上,看谁认识上面的笔迹。几天以内,三个从来没有见过彼此的人给警察局打了电话,说笔迹属于一个没有执照的铝线安装工,他给他们三个人都施过工,但他们都不满意。铝线安装工被拘捕、审判,并被判处一级谋杀罪。
波尔德市警察局的警探们看起来挺喜欢这个点子。
我问他们想不想听听我的建议,在抓到嫌犯后怎么审讯他。他们说好的。这种情形有些怪。我是和拉姆齐的律师一起来的,却在告诉警方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手段,而我知道这些手段很可能会被用在这位律师的当事人身上。我建议在审讯室摆上犯罪现场的物品和道具,这样凶手在看它们的时候就会不小心流露出一些身体语言。这之所以很奇怪,是因为我真的认为应该这样做,但是我知道,如果布赖恩·摩根回去以后同约翰和帕特茜讲了我的话,那么如果他们是罪犯并被叫来讯问的时候,他们要比不知道这个手段的情况下更难避免这些“道具”的影响。不管怎么样,覆水难收。
我继续说,拉姆齐夫妇想和警察局深谈,但是律师们担心局长会对他们测谎,即使在科罗拉多州测谎结果不能当做证据。我解释说我的小组和我本人从不认为测谎有太大作用,我们认为这只是一种讯问的手段。我说测谎的结果太不确定,并且任何人如果觉得没有尽到保护自己孩子的责任,例如约翰·拉姆齐就这么认为,那么在事情发生后这么短时间就做测谎,结果一定是他说了谎。另一方面,仇视社会的人在测谎中的结果反倒很好。如果一个人没有良心,可以对别人撒谎,那对测谎机撒谎就更不会有问题。即使测谎“有效”的时候,它所测到的也只是被测者内心的一种确信,而不是事实。我敢说我相信O·J·辛普森可以通过测谎实验,因为他已经说服自己他的所作所为是合理的。实际上,当戈德曼家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律师丹尼尔·佩德罗塞利向我咨询的时候,我还曾告诉他不要进行测谎。
在2000年早春,这件事情再次引发了争议。拉姆齐夫妇在全国电视节目上说他们从来没有被正式要求参加测谎,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下完全愿意接受测谎。我相信,实际上,他们急于证明自己清白,所以他们没有同律师商量,而律师和我却非常理解测谎的实质。但是话一经拉姆齐夫妇说出,律师们就无法把话收回,否则会出现新的公共关系危机。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了一个大家都不满意的解决办法:进行一次私人的测谎实验,但是这个过程中没有联邦调查局成员参加。我相信时间已经足够长,所以约翰·拉姆齐应该对案件有了新的观点,应该不会因为其他的因素而不能通过测谎,但是我认为这并没有使我的观点有任何的改变。
我第一次去波尔德市一共和这两位警探呆了两个小时。见面过后,布赖恩·摩根和我都认为这次见面很有成果。
我当天下午离开了波尔德市,摩根说他很可能会再给我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