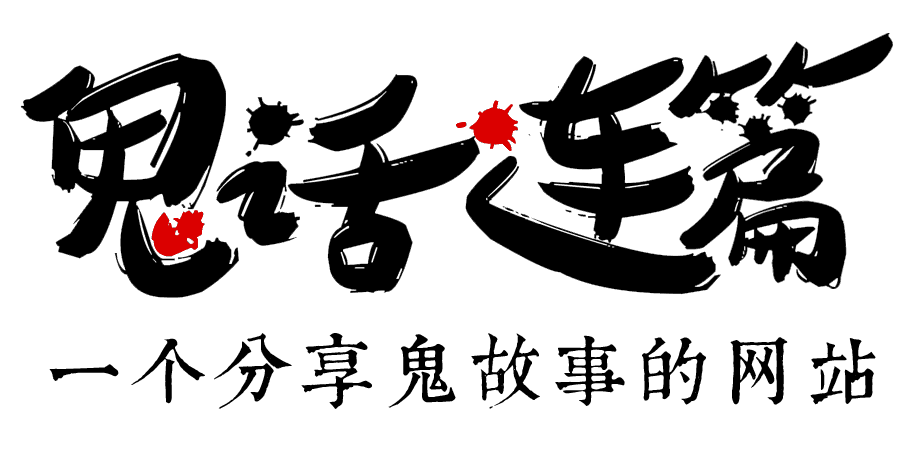如果说伊丽莎白·肖特代表了美国梦那非常脆弱、陈旧的一面的话,那么劳伦西亚·本姆本尼克则代表了美国梦更加坚实、更加现代的一面。然而,劳伦西亚的故事同样是一个令人伤心不已的悲剧。
同样地,在劳伦西亚·本姆本尼克的生活中,虚构和现实交织在一起。她称自己为劳丽,但是公众更知道的是班比这个名字:她是一位来自中西部的美丽的金发女郎,曾经在花花公子俱乐部工作,后来她成了一位有能力的、坚强的职业女性,成功打入传统上全是男性的警察行业。她激发了人们的罗曼蒂克式的想象:一位遭受极大冤屈的美女,被判犯了她发誓从未犯下的罪行,接着就被监禁。但后来一个英俊的王子救了她,助她逃离监狱,并且给了她真爱。她开始逃亡,整个逃亡过程都被压缩在“快跑,班比,快跑!”这样的一个口号式的句子中。这句话出现在报纸头条中、T恤衫上和脱口秀中。即使是这句短话也体现了这个故事中的内在矛盾,让人想起典型的迪士尼电影所表现的人的本真的迷失。这个绰号实际上是男性警员给她取的,当时她是一个警察学员。
尽管现实和上述情况有着重大差别,但同样让人困惑不安。
1981年5月28日,刚刚过凌晨二点三十分,威斯康星州警方对密尔沃基市南部西拉姆齐大街一七○一号打来的紧急电话迅速作出反应。十岁的肖恩·舒尔茨和他八岁的弟弟谢南·舒尔茨开门让他们进到屋内。在卧室内,警方发现这两个男孩的母亲、三十岁的克里斯廷·琼·舒尔茨面朝右侧卧在床上,明显已经死亡了。她有着深褐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身穿一件黄色的阿迪达斯T恤衫和白色裤子。T恤衫右肩部被撕开了,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枪伤。晾衣绳把她的双手捆在身前,一方蓝色的大手帕式的头巾蒙住了她的头,堵住了她的嘴。没有任何人闯入室内的证据,屋子的门都结实异常,而且锁死了。屋子所在的街道照明也很好,和其他房子靠得很近,可以说周围一带都很安全。然而,这所房子确实背靠着一座高速路天桥,后门比较隐蔽,很难看到。因此高速路可能就是闯入室内的罪犯的逃离线路。
两个小时之后验尸员才到达现场,救护车则还晚了一个小时才到。当警方把被害人的尸体包裹起来准备运输的时候,他们从她的小腿那里拿下了一根褐色的头发。
肖恩告诉警方,他醒来的时候发觉脖子好像被绳子捆住了,而脸则被一只戴着手套的大手给蒙住了。他于是开始挣扎并发出尖叫,然后他听到那个人发出了很低沉的一声咆哮,并跑过了走廊。肖恩和弟弟来到走廊上,发现母亲的卧室里有一名男子。
谢南说那个白人男子很高大,扎着很长的马尾辫,穿着绿色的跑步服。他说这个男子手上拿着一把枪柄为珍珠色的手枪。谢南听到他母亲的卧室里有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上帝呀,请不要这样做!”然后就听到一个像爆竹爆炸一样的声音。
当这名男子跑过他们身边,仓促地跑下楼梯时,他们俩都注意到他穿着绿色的军用夹克,还穿着一双黑色的皮鞋,就好像警方穿的那种。在这一点上,这两个孩子应当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因为他们的父亲(克里斯廷的前夫弗雷德)还有妈妈当时的男友都是警察。
肖恩跑到他母亲身边,当时她还活着。他撕开了妈妈的T恤衫,希望能够处理她的伤口。大约凌晨二点三十分,他打电话给妈妈的男友、四十一岁的司徒尔特·霍内克,叫他过来帮忙。肖恩记得霍内克当时说:“我知道这肯定会发生的。我认为肯定是弗雷迪干的。”
霍内克打通了警方的紧急电话,然后立即就冲到克里斯廷的屋子里来了,陪伴他的有他的室友、同是警察的肯尼斯·赖特考斯基。他们几乎和霍内克打电话叫来的巡逻车同时到达。进到屋内之后,霍内克马上就冲到楼上,翻动她的身体来看看她的具体情况。霍内克作为被害人的男友,在接到受了惊吓的两个孩子打来的电话之后立即赶过来,然后有这样的举动,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从技术角度来说他破坏了现场。这不过是这个案件中发生的一系列的侦查失误之一。
在此前一年的11月和克里斯廷离婚、终止了他们之间持续十一年婚姻的艾尔弗雷德·O·弗雷德·舒尔茨当晚正在执勤。他得到了谋杀案消息,来到了犯罪现场,当时克里斯廷还在屋内。这里,我同样很能理解为什么他想到犯罪现场来,特别是当他的两个儿子在那里的时候。但是,我认为他本应被阻止进入现场的。作为她的前夫,尽管他当时执勤因此不在犯罪现场,但他还是可能被当作嫌疑人。然而,我非常了解警方为什么通知他来到现场,因为在涉及某个警察家人的无数案件中,这种现象我们已经看得多了。其他警察认识他,知道这两个是他的孩子,这是他的房子,等等,并且还把他也看作一个被害人。这是一种自然的、正常的反应。
舒尔茨打电话叫醒了他当时的妻子、年方二十一岁的劳伦西亚·本姆本尼克,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他和他的搭档警官麦克尔·德尔菲开车到了他和劳丽的公寓,那里离犯罪现场十六个街区。弗雷德当时用手感觉了一下她的汽车发动机罩,据他后来说,发动机罩是冷的,并且在德尔菲在场的情况下,他检查了那支三十八毫米的备用左轮手枪。德尔菲闻了闻,并且自己对之作了一番检查。手枪上有灰,因此德尔菲断定这支手枪当晚没有开过火,而且最近也没有被擦拭过。弗雷德要劳丽和他一起去认被害人,也就是他的前妻。他还把那支备用手枪放进了他的公文包中。后来证明这里发生了另外一个侦查失误,弗雷德忘了在刑侦实验室登记他的这支备用左轮手枪,而后来就是这把左轮手枪被断定为杀人凶器。这把手枪的号码没有登记,并且案发后长达三个星期之久,那把手枪都在他那里,之后他才将它交上去检查。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大约是凌晨四点钟,有两个警官来到舒尔茨和本姆本尼克的公寓,问劳丽是否有枪或者绿色的跑步服,然后还问了一些有关她丈夫和司徒尔特·霍内克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个人曾经是室友。然后,当时有人称弗雷德很不高兴霍内克去约会他的前妻,他们俩都非常不喜欢对方。
就劳丽这边而言,她说当谋杀案发生时她单独在公寓中睡着了。那天晚上,她一直在打点行李,因为他们准备搬到一个小一些的公寓去。她当时还计划和一个朋友出去,但是后来他们之间的约会被取消了。
警方推断出了克里斯廷·舒尔茨最后一晚的生活。那天晚上,她给霍内克准备了晚餐,他们一起喝了点酒,大约晚上九点钟才吃完。然后两个孩子就上床睡觉了。他们两个大人则在看电视,之后克里斯廷开车送霍内克回家。霍内克的家距离克里斯廷的家大约只有三分钟的车程。另外一种说法是,当时霍内克是自己回家的,克里斯廷让他出去时顺手把门关上。
该地区内的十二名居民,其中包括两个警察,曾经看到一个符合孩子们描述的男子在谋杀案发生的几个星期前在这里跑步。他头发红棕色,扎着马尾辫,穿着绿色的跑步服,身上还有一方蓝色的大手帕,和堵住被害人嘴巴的那块大手帕很相像。在离现场一英里的地方工作的两个护士曾经注意到,案发的那天凌晨大约二点五十分的时候,有一个男子躺在停车场里。他们打电话叫警察,当他们返回时,发现一个头发红棕色、身穿蓝色跑步服的男子站在灌木丛中。被害人的邻居赖伊·库加瓦告诉警方说,案发当晚他呆在他的一个朋友家中的时候,有人潜入了他的车库里偷走了一把三十八毫米的手枪和一件绿色的跑步服。
伊莱恩·塞缪尔斯医生进行的尸体检验表明,凶手是把枪顶着被害人的背、贴着被害人的皮肤开火的。子弹穿过她的右肩,直接射入了心脏。此种性质的接触射击会有一种“回溅”效果,也就是说伤口处的血和组织会溅到枪管中去。
克里斯廷的朋友和亲戚都说她是一个运动健将,身体健康,喜欢户外活动。据称她还是很有脾气的,如果凶手不是用枪顶着她的话,她是不会让凶手用绳子把手捆起来而不反抗的。她的指甲下面和楼梯顶部两边的墙上都有血迹。
从这里开始,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尽管弗雷德的搭档此前已经说弗雷德的手枪没有开过火而且最近也没有擦拭过,但是地区刑侦实验室的弹道分析表明,那把三十八毫米的、枪管长四英寸的史密斯维森左轮手枪上面沾有A型血,弗雷德和克里斯廷的血型都是A型,并且杀死克里斯廷的那颗子弹的弹片上的划痕和枪管内的斑纹相吻合。在谋杀案发生之后,在弗雷德屋内找到了一盒二百格令的斯皮尔子弹,他说这盒子弹是他的。斯皮尔子弹是密尔沃基警用手枪的标准子弹。全国知名的弹药专家蒙迪·鲁茨也说,弗雷德的那支手枪的斑纹和打死克里斯廷子弹上的划痕高度吻合,已经足以得出确定的结论了。其他分析人员也宣称那颗打死克里斯廷的子弹只可能是从她前夫的手枪中射出来的。这样,弗雷德和劳丽都成了嫌疑人。
这样的案件中,前夫经常都被认为是嫌疑人,至少侦查刚开始时是如此。弗雷德·舒尔茨可以说有作案动机。克里斯廷和孩子们高高兴兴地住在他建造好的房子中,而他和劳丽则住在一个狭小的公寓里。此外,由于他要支付赡养费、孩子抚养费以及房子的抵押贷款,必须控制开支,为此这对新婚夫妇还曾在一段短时间内和一个名叫朱迪·泽斯的朋友一起合租过一所公寓。根据劳丽的说法,弗雷德对离婚和解协议的金钱数量感到非常痛恨。他抱怨说,他的前妻得到了一切。据称,克里斯廷曾经告诉她的律师,说她很害怕弗雷德,说他曾经威胁她的生命,并且还想继续控制她和两个孩子。她还认为自己被人跟踪了。当然,离婚案件中出现糟糕的感觉和激烈言辞这都是很常见的,而且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弗雷德按他所说的去做了。
劳丽被警方当作一个更大的嫌疑人,因为弗雷德的备用手枪就是杀死克里斯廷的凶器,而弗雷德当时不可能在犯罪现场,可是那晚劳丽却一个人呆在家中,可以拿到那把手枪。而且,当弗雷德的律师建议她不接受测谎时,她就拒绝了测谎,而弗雷德却同意并接受了一次测谎。他通过了测谎,但是结果却是毁坏性的:他承认过去曾经殴打过克里斯廷,曾经就超速罚款单问题说过谎,而且在案发当晚他身在何处这个问题上,他也没有讲实话。
此外,以下这一点也与常规情况不符:弗雷德·舒尔茨的搭档麦克尔·德尔菲没法提供他们俩当晚的工作日志。后来警方了解到,尽管他们俩说当晚在调查一桩入室行窃案,但实际上却是另外两个警官在调查那桩案件。舒尔茨和德尔菲则在案发当晚去过好几个酒吧泡吧,可他们是在执勤呀!虽然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舒尔茨当时不在现场,但测谎结果至少都是令人尴尬的。
间接证据不断累积,人们则逐步将劳丽·本姆本尼克想象成一个诡计多端、贪婪无耻的继配太太。朱迪·泽斯的母亲法兰西斯宣称,案发前几个月一次吃晚餐的时候,她曾听到劳丽说要让克里斯廷“滚蛋”。朱迪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她强调这是因为弗雷德给了他前妻太多的钱。根据朱迪的说法,劳丽曾经找到朱迪的男友托马斯·格特纳,说让他去找个什么人把弗雷德的前妻“除掉”。此外,劳丽确实有一方蓝色的大手帕和一根晾衣绳,和犯罪现场发现的很相像。许多人还说劳丽确实有一件绿色的跑步服(包括朱迪·泽斯也说,在以前她和劳丽与弗雷德共住的那个公寓中,确实有那么一件绿色的跑步服),尽管警方没有发现任何此种服装。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的案件中已经看到的,各种说法和线索都指向不同的方向。根据伊莱恩·塞缪尔斯的结论,尸体上和那方大手帕中发现的头发和被害人的头发一致。但是来自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头发分析专家戴安·汉森则认为,那两根头发和从劳丽·本姆本尼克的梳子上找到的头发样本是一致的,那把梳子是警方从劳丽那里收缴下来的。
然而,这个证据是有疑问的,并且可能是有人栽赃。1991年出版的《多伦多之星》中引用了一封写于1983年的信,其中塞缪尔斯医生再一次肯定地说:“我没有发现任何金黄色的或红色的头发……我从尸体上找到的所有头发都是褐色的,并且和被害人的头发绝对一致。”
塞缪尔斯继续说道:“我不想说这个证据是他人栽赃的结果,但是我认为,当我封那个信封的时候,里面还没有什么金黄色头发,但是后来那个信封中却神秘地出现了金黄色的头发,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解释不通的。”然后塞缪尔斯认定:“这些偏离常规程序的现象,再加上参与调查的警方人员的敌对态度……迫使我只能认定,肯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劳丽和弗雷德的公寓内,警方发现抽水马桶上挂着一顶红褐色的假发。不仅假发的颜色和舒尔茨的两个孩子对那个闯入室内的人的头发颜色描述是一致的,而且假发也和在被害人身上发现的头发是一致的。但即使是这个证据也令人觉得疑问重重:他们俩的房间和另外一间房间共用一个卫生间,而且住在那个房间中的女士曾经说,朱迪·泽斯曾经来过她那里,并说要用一下卫生间。朱迪·泽斯之后第二个用卫生间的人就发现抽水马桶堵住了,后来从里面找出了这顶假发。朱迪·泽斯后来承认她确实有一顶褐色的披肩假发。劳丽则说,朱迪·泽斯的男友托马斯·格特纳为他最好的朋友、一位当时不在执勤的警察的死而一直对弗雷德心存怨恨,因为是弗雷德将他打死的。劳丽说,通过陷害他们,托马斯·格特纳等于报仇雪恨了。
尽管如此,大部分间接证据都对劳伦西亚·本姆本尼克不利。1981年7月26日,她被指控犯有对克里斯廷·舒尔茨的一级谋杀罪,作出此种指控的主要根据是她能够接触凶器,而且无法肯定地证明她当晚不在犯罪现场。因此,尽管她、弗雷德、朱迪·泽斯、托马斯·格特纳和房东都有那个房间的钥匙,当谋杀案发生时,劳丽是一个人在房间内的。并且,警方相信,她以前曾是警察,因此应当知道如何掩盖她的行踪,并且她高大强健,通过乔装改扮,她完全可以轻松地骗过克里斯廷的两个孩子,使他们俩认为她是个男的——尽管肖恩坚持说,他所看到的确实是一个男子,甚至还做证说那个男子根本不可能是劳丽。
劳丽·本姆本尼克于1982年1月24日出庭接受审判。法庭上的人们和媒体都注意到她的美貌和女权主义倾向,这让许多人断定,班比之所以被人指控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因为克里斯廷·舒尔茨之死,又是因为她的此种形象。巡回法官麦克尔·斯奎尔劳斯基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程度上依赖于间接证据的案件了,其中许多间接证据都可能不能认定她有罪。但是从整体上看,陪审团只可能作出一种结论。”
法官斯奎尔劳斯基所说的此种证据上的含混不清的例子之一,就是杀人凶器本身了。1990年7月31日,记者罗杰斯·沃金顿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劳丽·本姆本尼克案件的文章:“弹道测试的结果是,从舒尔茨那里收缴来并在6月21日测试的那把枪确实就是杀人凶器。但是在审判过程中,舒尔茨和德尔菲都无法完全肯定,在法庭上出示给他们看的那把枪就是他们在案发当晚所见过的那把枪。”
由五位男士和七位女士组成的陪审团讨论了三天半,最终认定劳丽有罪,并在3月9日宣布了陪审团的判决。她被判处终身监禁。在泰契达行为矫正所,劳丽继续说她是无辜的,宣称被密尔沃基警察局陷害了,目的是为了不让她向外界泄露警察局中某些成员吸食毒品、淫乱和滥用政府拨款的行为。这是班比传说中一颗重要的试金石。要明白为什么研究这个案件的人中有如此多的人认为她是被冤枉的,我们就必须对她的背景有一些了解。
劳伦西亚·安·本姆本尼克是居住在密尔沃基的约瑟夫和弗吉尼亚·本姆本尼克夫妇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约瑟夫曾经是密尔沃基警察,但是干了三年之后离开了密尔沃基警察局,因为他看不惯局里存在的普遍的腐败。后来他成了一个木匠。劳伦西亚长大成人后想成为一个兽医,但是却由于没有相关文凭而无法实现。她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服装推销大学课程,后来打各种短工来挣钱,比如做模特和有氧运动教练。她身材很高挑,容貌漂亮又体态健美,做这些是毫不令人奇怪的。她曾身穿线条优美的服装出现在施莉茨酿酒公司1978年的挂历上。她出现在3月份那张挂历上面,因此也就是“三月小姐”了。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有关她的种种传闻开始了。
她还持有许多强硬的女权主义观点,并且于1980年进入了密尔沃基警察学院。从一开始她就感觉到,作为男人世界中的一个女人,她经常遭受各种骚扰。
正如克里斯·拉迪什在她的著作《快跑,班比,快跑》中所写道的,劳丽和当时也是新警员的朱迪·泽斯还有其他三个朋友一块去听了一场音乐会。当劳丽正在女厕所的时候,朱迪被两个便衣警察逮捕了,因为她携带大麻。第二天,劳丽·本姆本尼克的教官(另外一个警察)把她叫到办公室,对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严加盘问。因为朱迪椅子下面的一个杯子中发现了一小截亚麻香烟,她被开除了。而劳丽则继续受到上司的严厉拷问,希望她会坦白说她吸食了毒品。劳丽拒绝坦白她没有做过的事情。看起来就是因为她是个女性,所以才受到如此不公对待。但是1980年7月25日,她以全班第六名的成绩从密尔沃基警察学院毕业,并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警徽。
她被分配到第二区,那里犯罪不是很多。她马上就被她眼前所看到的场景吓呆了:不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警察局内,到处都是贪污贿赂,警员们在执勤时喝酒、吸食毒品、和妓女口交,还虐待嫌疑人。尽管如此,她还是很自豪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警察,而且喜欢出去巡逻或者自己一个人出去工作。
8月25日,从密尔沃基警察学院毕业才一个月,劳丽在家中接到一位警官打来的电话。警官告诉她,她被解职了。她根本就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两个警官来到她的住处,缴走了她的警徽、手枪和制服。警长哈罗德·A·布莱尔那个星期总共无缘无故地解雇了三名女警察,其他两个是黑人,她们三个当时都处在见习期。警长对此作出的唯一解释是,解雇她们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警察工作”。
根据几天之后出版的《密尔沃基日报》的报道,劳丽“被指为人不诚实、提交虚假工作报告,但是除此之外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细节”。
几个星期之后,当她终于有机会看个人档案时,她发现朱迪·泽斯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那份文件说在那天的音乐会上劳丽确实也吸食了大麻。朱迪承认自己在上面签了名,但她是在遭受连续多个小时的审讯之后,在他们的胁迫之下才这样做的。她们两人都对她们的被解雇提起了申诉,劳丽也原谅了朱迪,并约定两人共同采取行动。
在等候申诉结果的时候,由于急需用钱,劳丽就在日内瓦湖花花公子俱乐部做了一名女侍者。她只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星期,但是这份短期工作却进一步增强了她在外人心目中的混合形象:坚强的警察、美丽的性感尤物。就像对待伊丽莎白·肖特一样,公众心目中所看到的和她的实际生活截然相反。
美国司法部长詹姆斯·莫里森开始调查对密尔沃基警察局的种种指控,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滥用了巨额的拨款资金以及毫无根据地解雇少数族群的警员。劳丽对莫里森说,通过先雇用女警员但是马上又解雇她们,密尔沃基警察局既满足了联邦政府规定的人员指标,又得到了联邦政府为此而给警察局的种种拨款。她开始起诉密尔沃基警察局,指控它性别歧视。1980年10月,她收到了一些照片,上面是全裸男警员在一个公园中跳舞的情景。在她将这些照片交到内务处之后,她的汽车轮胎被人砍裂了,并且挡风玻璃上有一只死老鼠。而且她还不断接到有人在深夜打来的电话。或许应当注意的是,当劳丽被指控犯下谋杀罪时,联邦政府对密尔沃基警察局的调查就不了了之了,而原本她是此次调查中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姆本尼克于1980年12月遇到了弗雷德·舒尔茨,当时他和克里斯廷离婚才一个月。约会大约几个星期之后,弗雷德向劳丽求婚。后来他们俩于1981年1月30日结婚。
因此,劳丽·本姆本尼克可能不是被当作一个正常的谋杀案嫌疑人来对待的,这并不难看出来。我以前说过,一个人是不会在一夜醒来之后就突然决定行凶的。在本姆本尼克案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劳丽·本姆本尼克因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而身陷孤立无援的境地。她看起来似乎认为警察应当符合更高的行为标准,而她的行为则让她大大吃亏。
这是不是意味着本姆本尼克是不可能有非法行为或暴力行为呢?不是的。但是我认为这使得她不大可能如此冷酷地杀死两个年幼的孩子的母亲。
然而,为了公正地作出分析,我们应当先从案件本身着手。我们首先来看看被害人的情况。我总是强调的是,我们应当从命案发生之前的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中被害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始。
克里斯廷·舒尔茨呆在自己家中,周围是一片很安全的地区,这使得她成为此种暴力犯罪对象的危险性比较低。但是她曾经觉得她好像被人跟踪了。如果她的前夫确实如她所说控制欲极强,而且,如果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她当前的男友有酒瘾,那么此种情况可能导致她与他们关系困难,这会使得她成为此种暴力犯罪牺牲品的可能性增大。
这宗谋杀案看起来似乎是毫无道理的。我的意思是事件发展的顺序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为什么无名罪犯要先进入作为母亲的克里斯廷的卧室,然后再去孩子们的房间中,此后又回到克里斯廷的卧室来把她杀死呢?罪犯可能担心枪声会惊醒孩子们,因此不得不先对付他们,这可能是有道理的。但是本案中的情况并非如此。让我们假设罪犯突然袭击躺在床上的克里斯廷,并威胁她说如果她叫醒他们的话,他就把他们杀了,从而迫使克里斯廷就范。接着罪犯将克里斯廷捆绑起来。那么,这之后他为什么要将克里斯廷一个人活着留在卧室,到孩子们的房间中去呢?这非常不符合逻辑,也看不出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让孩子们活着并不吵醒他们是罪犯迫使克里斯廷合作的最佳手段了,这比捆绑或用武器威胁强多了。
当罪犯离开克里斯廷的房间,据称是个运动健将的克里斯廷应当会本着母亲的本性去保护她的两个孩子。至少,她会在罪犯有机会勒死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之前发出尖叫,叫醒他们。这让我怀疑现场应当还有另外一个罪犯。当其中一个罪犯走到孩子们的房间中去时,是这个罪犯在看着克里斯廷。
有人曾经推测,罪犯做的这一系列事情就是为了让孩子们醒来,并且能离罪犯足够近,最后好让孩子们肯定地说明哪个人不是罪犯。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肯定,但这确实是对被害人被杀的奇怪过程的一种解释。用大手帕把被害人蒙住,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可能是罪犯用来误导侦查人员的一个因素。
这将我们引到犯罪动机这个更大的问题上。首先,看起来这不大像是抢劫,因为案发时间对罪犯来说非常危险,而且任何迹象都显示罪犯是专门针对被害人的。如果克里斯廷·舒尔茨听到什么响动,她应当会死在某个其他地方(她过去查看发出响动的那个地方),而不是在床上。甚至她可能还会给警方打电话。而且我们也可以排除性犯罪的可能性,因为现场没有什么性犯罪证据,而且那个无名罪犯实际上一度离开了被害人,走到孩子们的房间中去了。
因此这不是抢劫谋杀案,也不是强奸杀人案,但是克里斯廷·舒尔茨为什么会死呢?又会是什么样的人将她杀死的呢?
首先,要进入里面有三个人的房子中去,这是需要胆量的。这说明我们面对的罪犯是一个熟练潜入室内的人。现场没有发现什么强行闯入的痕迹,因此罪犯要么有钥匙,要么知道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屋内。如果罪犯有钥匙或者对屋子熟悉的话,那么他可能知道被害人曾是一位警官的前妻,当时还是另一位警官的女友。他会想到她自己可能就有一把手枪。难道他是个傻瓜吗?根据这宗案件对罪犯的危险程度,以及这宗案件的作案方式来看,这个案件不会是那种女性罪犯(甚至包括强健的、女权主义的罪犯)犯下的与个人原因有关的杀人案,我可以很有把握地断定,劳丽·本姆本尼克不大符合这里的行为特征。
我之所以认为对本姆本尼克的审判有疑问,还在于我没有看到本姆本尼克有控方所称的那种动机。难道我不认为如果她能有更多钱的话,她会感觉更高兴一些吗?不是的。有了更多的钱,谁不会更高兴呢?但如果她如此冷血,能够为了钱而杀人,那么她肯定也会将两个孩子杀死。她可不想马上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不论她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此前如何。她刚刚结婚。尽管克里斯廷住的那间房子确实不错,但是案发之后,弗雷德和她之间就她为什么不想搬到那里去发生了激烈争吵。我们认为,如果她是个冷血杀手的话,她可能只会作一点不同表示,以摆脱嫌疑,而不会冒毁坏她与丈夫之间关系的风险。
我认为,如果要说劳丽·本姆本尼克是出于贪婪这一动机而杀人的话,那么她的此种贪婪可能早就影响了她与丈夫弗雷德的关系。我们可能会听到某些证人说,他们之间表面上看起来恩爱非常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开始貌合神离了:因为他对失去了房子极端不快,或者他们的金钱困境几乎毁了他们之间的任何事情。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与世界上无数没有善终的浪漫爱情不同,本姆本尼克和弗雷德·舒尔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更是弗雷德这方对婚姻失败的回弹反应。他和克里斯廷的婚姻持续了十几年,并且离婚之后几个月就和劳丽结婚了。当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认识的时间还不长。无论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是多么真挚,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都还只是一种全新关系,会带有某种表面性。
我们可以说劳丽本意并不想杀死她丈夫的前妻克里斯廷,但是当克里斯廷认出她来之后,她只好将克里斯廷杀了,但是这样说似乎更没有道理。首先,就像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此种假设和罪犯的作案时间顺序不一致。并且,特别是对于一个受过训练的警察来说,事先假定三个人中没有一个人会认出她来,这未免也太危险了。再者,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话,我们还可能看到某些其他事情,比如电视机被拿走了,或者被害人的衣服被扯下来了,这样的话看起来就好像不是因为个人恩怨的凶杀了。很明显,我们不认为像本姆本尼克这样受过训练的警察会把证物(比如假发)随处一扔,致使侦查人员马上就发现她有作案嫌疑;她也不会忘记给自己找一个不在犯罪现场的理由。
那么,如果克里斯廷·舒尔茨不是劳丽·本姆本尼克杀的话,凶手又会是谁呢?当侦查线索如此繁多,指向许多相互冲突的方向时,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然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像这种因个人恩怨而发生的谋杀案,凶手可能会是一个很容易被警方认定为嫌疑人的人,而凶手自己也应当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肯定会努力给自己找好案发时不可能出现在现场的证明。
劳丽·本姆本尼克的故事并没有随着她被审判、被定罪、被监禁而终结。1983年,威斯康星州上诉法庭维持了有罪判决。四个月之后,她和弗雷德申请离婚,于1984年6月被正式准予离婚。在审判过程中,弗雷德对她很支持,并且为她准备了辩护基金。但是在上诉法院作出判决之后,他则说他开始相信她确实就是凶手。
本姆本尼克连续几年都努力争取案件重开审判,但是都没有成功。同时,她继续激发着公众的激情。据称有几个男子被她冲昏了头脑,或说被她的外在形象冲昏了头脑。其中一个人甚至还雇了一个已经坐牢的杀手向警方“坦白”克里斯廷是他杀的,好让劳丽·本姆本尼克能够离开监狱。但是当控诉人员拒绝给予他豁免时,他也就没有“坦白”了。
她的名声也带来了一定积极影响。只要人们对她感兴趣,就会不断有人来研究她的案件。研究她这个案件的人中,有一位名叫埃拉·罗宾斯的密尔沃基私人侦探,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调查克里斯廷谋杀案。在罗宾斯和本姆本尼克因案件调查的开支问题而关系破裂之前,罗宾斯发现了许多可能证明本姆本尼克无罪的证据,后来律师们就曾利用这些证据来为她争取新的审判。
1990年7月15日,她的故事进入了新阶段:她从监狱洗衣房的一个小窗户爬出来,和她同囚室的另一个囚犯的弟弟、她的英俊的男朋友多米尼克·古戈里亚托一起逃亡。她可能是想通过逃离监狱来获得一种正常的生活,同时这一举动也让她轰动一时。打电话到威斯康星州一个很受欢迎的广播节目中的人里,有72%的人说,如果他们知道她在那里的话,他们是不会报告警方或者将她送回警察机关的。对她的案件的报道,包括那句口号“快跑,班比,快跑”,迅速扩大到威斯康星州之外的很多地方。
这对情侣到达加拿大的雷湾市三个月之后就被捕了,原因是“美国最大通缉犯”节目播出后,她在当地一家餐馆做女服务员的行踪被人举报了。
有趣的是,本姆本尼克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向加拿大政府申请难民资格,她说她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她无罪的情况下还不能重新获得审判。在支持本姆本尼克的力量和美国及加拿大当局之间发生了几次法律交锋之后(其中包括美国司法部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调查),本姆本尼克最后被遣返回了密尔沃基。
本姆本尼克的律师们提交了一份要求重新审判的动议,内容包括多个证人的口供,他们说职业罪犯弗里德里克·霍伦博格曾告诉他们,是弗雷德·舒尔茨给了他一万美元让他去杀死克里斯廷的。霍伦博格后来收回了他以前说过的话,之后不久就在1991年的一次未遂抢劫及绑架事件中自杀了。
律师们还得到了两个法医病理学家的专家证言,他们说那把让本姆本尼克背上罪名的手枪的枪口和被害人身上的枪口印不一致,因此那支枪不可能是杀人凶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代表政府的律师出示了一位著名的枪伤专家作出的与前一种意见相反的结论。但是至少可以说,此种往来交锋证明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面对霍伦博格原来的说法、手枪问题上的争议以及辩方提出的其他证据,再加上对自己有利的证人因为时日已久之故都已经去世了,地区检察官不得不准备和本姆本尼克达成交易。劳丽也害怕新审判可能会来得太迟。她想陪伴年迈的父母,于是她就同意了。
1992年12月,警方取消了她以前被定的罪,同时她对警方提出的二级谋杀指控不提异议。这样,根据她已经在狱中服刑的时间,她获得了假释。最近一些年,她几近破产,诉讼缠身,而且还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患上了丙型肝炎。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曾想采访她,但是她回绝了。我对她的做法表示理解。不论是被人看作有罪还是无辜,她的整个成年生活都处在这个案件的阴影以及这个案件所创造的她在公众眼中形象的影响之下。我们这里用多年以前她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来结尾。当时,她最后说道:“我已经厌倦了做劳丽·本姆本尼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