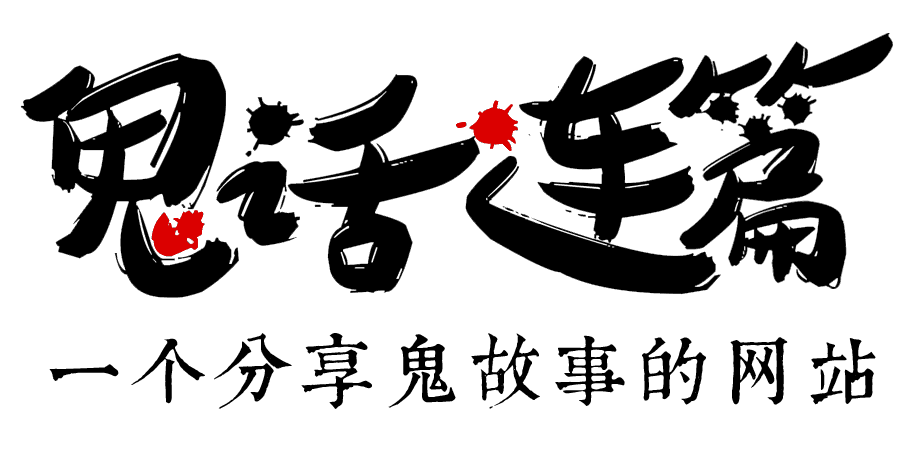10月11日,星期六,雾蒙蒙,晚上九点三十分。出租车司机保罗·李·斯代因在旧金山的吉尔雷大街搭载了一名乘客。实际上当时斯代因刚刚接过第九大街的一个乘客打来的电话,但是他的车被困在这片戏院区内到处拥挤的人群里了。当这个单身乘客走到他的车边要求乘车时,他要求去的地点正好是在去第九大街的路上,因此斯代因才让他上车。斯代因在他的日志上记下乘客要去华盛顿大街和枫树大街十字路口,然后就开车往西奔向这片靠近普利西迪奥(3)的居民区。
尽管斯代因的日志上记的是乘客要去华盛顿大街和枫树大街十字路口,但是最后却停在了再过去一个街区的华盛顿大街和樱树大街十字路口。到了这个地方之后,那名乘客不是付钱下车,而是近距离地朝斯代因的右脸开了一枪。然后他就爬到前排座位,拿走了斯代因的钱包。他还从斯代因的衬衫上扯下了一块布。但是他没有拿走斯代因的天美时手表、支票簿、戒指和他口袋中四美元多的零钱。之后他来到车外,将驾驶室中靠司机的窗户和后座左边的窗户擦干净。接下来他斜靠在汽车前后门之间的车身上,将靠着司机座位的那扇车门打开,把仪表盘擦干净,然后把门关上,大摇大摆地走入夜幕之中。
但是,罪犯不知道的是,整个过程被一个参加正在街对面举行的宴会的十四岁女孩看得几乎一清二楚。她当时是从离出租车大约五十英尺的一个二楼窗户上往外看的。当她意识到她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之后,就把她的两个兄弟叫到窗户边。这时,那个矮壮的白人男子正在擦那辆出租车,许多人都已经聚过来了,透过窗户看得清清楚楚。他们一直这样看着他,直到他走到拐角处,从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他是走着离开犯罪现场的。
同时,参加宴会的人中有人向警方打电话报了案。九点五十八分,接听电话了解了犯罪细节的接线员最后不知怎么回事把嫌疑人说成了黑人。因此当通信员将简要情报传给在大街上执勤的人员时,他们得到的对嫌疑犯逃走方向的描述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得到的对嫌疑犯外貌的描述却是错误的。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众说纷纭了。根据几个人的说法(这其中包括黄道十二宫在随后寄出来的一封信中的说法),正开着巡逻车巡逻的两个警员首先对警报作出了反应,几分钟之后就到达了樱树大街和杰克逊大街十字路口。他们看见一个矮壮的白人男子正朝普利西迪奥要塞方向走去。如果当时灯光更好一些的话,他们可能就能看到他身上的黑衣服上的血迹了。而如果他们知道嫌疑人是个白人男子的话,案件侦破情况可能大大不同了。但是由于他们被告知嫌疑犯是个黑人,因此他们只是问这个白人男子,是否看到什么可疑的人物。这个男子回答说,看到一个手中拿枪的男子顺着华盛顿大街往东跑去了。因此他们就往那个方向追去了。一个多星期之后,这些巡逻警才意识到,他们当时看到的可能就是嫌疑人,于是和一个肖像画家合作画出了嫌疑人的外貌草图。当罗伯特·格莱史密斯想对这里发生的信息沟通错误的情况进行研究时,他发现这几个巡逻警提交的报告被当作机密收起来了,旧金山警方的正式说法是,没有哪个警员曾经见过嫌疑人。但是此种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谋杀案发生之后的第二天上午,警方的肖像画家已经根据参加宴会的人提供的信息绘制了一份嫌疑犯肖像草图的情况下,后来还绘制了第二份嫌疑人肖像草图。
但是当时的警方没有意识到,此种擦肩而过本来也是警方让黄道十二宫露面的一个大好机会。警方应当发表一份声明,说警方正在寻求犯罪现场附近社区中这个可怖罪行的目击者的帮助。这份声明可以明确,警方很清楚,除了嫌疑人本人之外,当时犯罪现场还出现了其他几个人。警方希望他们能够向这些人了解情况,了解他们当时到底看到些什么。如果这个方法奏效的话,嫌疑人可能会向警方报告诸如此类的信息,因为他会认为,这样的话他当时出现犯罪现场的事实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而且如果当时确曾有人看见他的话,通过这样和警方接触,他也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
当警方到达现场时,他们发现保罗·斯代因朝副驾驶座位那边倒着,头靠在出租车的底盘上。里面有不少血迹,尽管车钥匙不见了,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里程表却还在运转。他们马上叫了辆救护车过来,并且向其他警员传递消息:嫌疑犯实际上是个白人男子。除了那两个首先作出反应的警员外,当时正往家里赶的谋杀案专家、督察沃尔特·克拉克在听到了警报之后,也马上赶到了现场。他的经验在这个案件中是很有用的,他当时立即让其他警员封锁了现场。当晚执勤的戴夫·托斯奇和他的搭档比尔·阿姆斯特朗到达现场时,救护车也已经到了,医生当场宣布斯代因已经死亡。克拉克通知了验尸官,并命令所有能够腾出来的警犬队出来搜索,此外他还从消防队调来了一架车载探照灯帮忙。
当侦查人员在现场作业时,徒步巡逻人员、警犬队和附近那个军事基地的军警联合展开了大搜捕。普利西迪奥离犯罪现场也就几个街区。附近的居民告诉警方,他们看见一个人穿过附近的操场,之后就潜入这个树木繁茂的军事基地去了。在随后的几个小时之中,泛光灯和手电筒把这个地方照得如同白昼。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搜捕停止了,这离斯代因被医生宣布因子弹击中大脑而死亡已经有四个小时了。尸体解剖过程中,从斯代因的大脑中取出了一颗严重爆裂的铜壳子弹,子弹直径九毫米。凶手只用他的半自动手枪开了一枪。此种子弹在这个地区是很少见的,在过去的三年中,整个基地只卖出了一百五十颗这样的子弹。斯代因右脸颊上的伤表明罪犯是直接用枪顶在他的头上开枪的。警方发现斯代因左手上有因为抵抗而留下的伤痕。
让我们来看看被害人的情况。被害人保罗·斯代因,二十九岁,已婚,在旧金山州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为了支付学费,除了晚上开出租车之外,他还兼作保险公司的推销员。他五英尺九英寸高,体重一百八十磅,一点也不矮小单薄。就他的个人生活、个人兴趣而言,除了开出租车本来就是高危险的工作外,没有什么东西表明他可能成为暴力犯罪的牺牲品。出租车司机的工作要求他们搭载陌生乘客,而且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要把乘客带到目的地。因为他们身边有现金,他们经常成为抢劫甚至更恶劣犯罪的目标。斯代因被杀的两个星期前,另外一个司机刚从出租车公司出来就被人抢了,并且一个多月以前,斯代因就曾被两个持枪歹徒打劫过。
实际上,初看起来,本案好像是一个不那么熟练的抢劫犯所做的一桩蹩脚的抢劫案。罪犯离开时满身是血,并且他没有拿走其他一些值钱的物品。当警方查明斯代因此前搭载乘客收取的费用之后,估计凶手拿走的钱顶多只有二十五美元。此外,他还留下了证据:当他把左手伸进去擦仪表盘的时候,为了保持平衡把右手撑在车身侧面上,这样留下了两个血指纹。
此外还有目击证人。那几个参加宴会的孩子说杀死保罗·斯代因的人是个白人男子,大约二十五六岁或者三十岁出头,金黄色短发,似乎是平头。他戴着眼镜,穿着黑色的裤子和皮大衣。他矮壮结实,大约五英尺八英寸高。警方向旧金山所有的出租车公司发出了记载此种描述的通知和嫌疑犯外貌草图,要求出租车司机警惕凶手以同样的手法再次作案。
警方张贴公告的同时,案件中出现的新情况证明这宗谋杀案可不是什么拙劣的抢劫案。10月,《旧金山新闻报》收到了一封信,上面的回信地址是一个符号:圆圈里面画着一个超出了圆周的十字。信的开头和以前收到的一封信是一模一样的:“我是黄道十二宫……”
写信人宣称斯代因是他枪杀的,并且提供了实物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他附上了从斯代因的衬衫上扯下来的一块布。然后他还提到了“湾区北部的那些人”,说他们也是他杀的。警方实验室证实,这块布料确实是从斯代因身上穿的那件衬衫上扯下来的。当托斯奇和阿姆斯特朗与纳帕县的警探纳罗见面时,纳罗认为杀死斯代因的凶手的笔迹和他正在追捕的凶手的笔迹一致,这一点后来得到谢伍德·默里尔的证实。谢伍德·默里尔是位于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市的“疑难文件处”的主任。
然而,警方在黄道十二宫案件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却没有丝毫效果。罪犯最新发出的这封信大肆嘲笑了斯代因被杀之后警方所作的抓捕行动:
旧金山警方本来昨晚是可以抓住我的,如果他们正确搜索公园,而不是开着他们的警车在公路上赛跑看看谁的车发出的噪音更大的话。那些开车的警察应当把车停下来,悄悄地坐在车中,静静地等我从我的隐身处溜出来……
他的这些话看起来起到了一定效果。旧金山警察局长马迪·李在媒体面前硬挺着头皮说,如果黄道十二宫当晚真的就在警察眼皮底下的话,他应当在信中提到警犬和手电筒。我认为,如果凶手就是与那两个首先作出反应的巡警说话的人的话,警方丢的面子可就大了。他几乎就要被警方抓住了,当时他肯定很害怕,但是他不会对警方承认这一点,也不会对自己承认这一点。因此他必须显得志得意满。像他这样的罪犯肯定会以过度贬低他实际暗中忌妒羡慕的人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卑微感。他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但是他必须认为,是他将警方大耍特耍了一番。
证明他比警方胜出一筹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找到另一种自己更能控制、更能显示自己强大力量的方式。当罪犯在结尾发出令人恐怖的威胁时,他的目的就完全达到了:
学校的孩子们可是很好的目标,我认为我应当在某个早上把一辆校车内的孩子都干光。先打穿前轮,然后当他们活蹦乱跳地走下车时,我就尽情射击。
《旧金山新闻报》和警方配合,几天之中都没有将这部分发表,只是发表了其他部分和警方绘制的嫌疑犯外貌草图。但是这不过只让马上就要到来的恐怖感晚了几天而已。整个洛杉矶、纳帕和周围地区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保护学生:校车上配备了另外一个司机,他可以随时注意发生的问题,并且当一个司机被射死的话,他可以顶替上来;在某些地方,甚至派了警察护送校车。伯丽爱沙湖的森林部门和巡逻警队的敞篷小货车都被派上了用场,甚至天空中还有飞机监视校车经过的路线。
我们当然必须认真对待这样一种威胁。很明显,这个人确实有能力杀人,我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但是我认为凶手发出这个威胁的真正目的,又只是为了将恐惧散布在公众心中,并操纵大众情绪。如果说伯丽爱沙湖谋杀案和旧金山谋杀案对罪犯来说已经很危险了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会比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一辆载满学生的校车射击更危险呢?对于罪犯来说,这几乎就是自杀。警方针对这个威胁而作出的所有努力只不过是为了挽救警方的面子罢了:罪犯确实可能不光是口头说说而已,但是警方也没有必要这样神经兮兮。
警方曾经试图通过媒体和黄道十二宫打心理战。加利福尼亚总检察长托马斯·林奇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向凶手保证警方会帮助他,如果他自首的话,他的合法权利肯定会得到完全的保障。林奇试图从黄道十二宫的虚荣心下手,说作为一个“聪明人”,他自己明白自己最后肯定会被抓住的,因此他应当明白投降是最好的选择。《旧金山监督报》也曾经作过类似的努力,但是都没能让那个杀人犯向警方自首。
此外,美国密码协会主席D·C·B·马什博士向凶手提出了一项挑战。马什用黄道十二宫用的那种代码写了一封信,信里面提供了电话号码,希望黄道十二宫能够在准备好了一份真正包括他身份的信件之后,就打那个电话。马什博士的挑战书发表在《旧金山监督报》上,一直没有得到响应。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和技巧,因为这可能很符合那个无名罪犯的个性。
斯代因谋杀案发生之后不到两周,旧金山正义厅内举行了一次大型会议。从瓦列霍、纳帕、本尼西亚、索兰诺、圣马特奥和马林来的侦查人员和联邦调查局、州刑事鉴定及调查局、海军情报处、加利福尼亚公路巡逻队、美国邮政调查局的代表,也就是任何参与案件侦破的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上,人们讨论了这些相互关联的案件,并比较了所有已经掌握的证据。
如果我当时参加了会议并得到了来自不同辖区的警方的合作的话,我会强调必须和罪犯打心理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在诸如这样的案件中曾经建议警方采取过的策略之一,在这个案件中却被罪犯采用了。
我可以想象在1969年10月末,当黄道十二宫看到媒体和新闻节目对他发出的攻击校车的威胁关注越来越少的时候,他肯定是在想他应当怎样摆脱此种状况。尽管我不一定能够预测他到底会做件什么事情,但是我可以肯定罪犯会做点什么让他重新回到万众瞩目的中心。他当时可能还对上次杀死斯代因之后差点被警方逮个正着而心有余悸(尽管他自己不会承认),因此他不大可能再次进行凶杀活动。但是由于他没有兑现他发出的威胁,因此可能感觉再发出另外一封类似的信的话就不会有什么轰动效果了。他所急需的是能让公众全部头晕目眩的惊世之举。
我曾经建议警方采用的策略之一是,在公众中找一个“同情”罪犯的人。我们知道大部分罪犯会跟踪媒体对他们的报道,因此根据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这个罪犯所属的类型,我会建议警方找一个能让罪犯以某种方式安心联络的人。比如,在警方要员不断谴责罪犯是个杀人狂魔的同时,让报纸记者采访一个著名精神病学家,他和警方的意见“完全”对立:“这个人可不是什么疯子。实际上,他极端聪明,这就是为什么警方没有抓到他的原因所在。但是他被人误解了……”然后让记者在他的办公室中拍下他的照片,并“顺带”提及办公室的地点,当然要确保他的办公电话号码和地址都出现在报纸上。然后警方就可以坐下来,静等罪犯和这个在他看来能够理解他向这个世界发出的讯息、能够向公众澄清对他的种种不正确的看法的人联系。
黄道十二宫后来的所为非常接近我的设想。某一天凌晨两点钟,旧金山海湾对面的奥克兰警察局电话铃声响了。电话里的人说他就是黄道十二宫,并要求和著名的刑事律师F·李·贝利进行电话交谈,或者,如果找不到贝利的话,当地著名律师梅尔文·贝利也行。打电话的人要求他们这两个人中至少要有一个人出现在当地在上午播出的一个脱口秀节目中。我觉得黄道十二宫的选择非常有趣。F·李·贝利可是名声在外,被人称作“脱罪之神”,他代理的超过一百宗杀人案件中,除了三次之外,都成功地让陪审团判决嫌疑犯无罪。而梅尔文·贝利则是因为成功地为杰克·卢比和米基·科恩这样臭名昭著的人进行了辩护而名声大噪。正如自此以后的多年时间所证明的,这两个律师都有吸引媒体注意的好能耐。很明显这正是黄道十二宫所需要的。
后来的情况是,F·李·贝利没法脱身,但是梅尔文·贝利那天上午出现在第七频道的脱口秀节目中,就坐在主持人吉姆·邓巴尔旁边。节目比平常提早了半个钟头。他们在焦急等待、观众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七点钟刚过,第一个电话打进来了,后来还打进来许多电话。打电话的那个人不停地挂断,然后马上又打进来,说他自己是“山姆”,并且对梅尔文·贝利和邓巴尔诉说自己是如何孤单、如何头痛。打进来的三十五个电话中有十二个被广播了,梅尔文·贝利带着一队警察和记者于当天上午十点三十分来到电话中约定的地点。读者可能已经猜到后面的一切了:“山姆”根本就没有出现。对这个人后来打给梅尔文·贝利的电话进行追踪之后,警方发现那些电话都是纳帕州立医院的一个精神病人打过来的。当初接到打进奥克兰警察局的那个电话的警员说,那天的电视节目中打电话给梅尔文·贝利的那个人听起来和打电话到警察局的那个人的声音不同。然而,就黄道十二宫而言,那天谁打电话给梅尔文·贝利一点都不重要。他得到了媒体的关注,而且是现场直播的节目。他成功地操纵了看电视节目的每个人,让整个地区都在焦急地等待他的电话。同时,在打电话给警察局的几个小时之后,让一个著名人士俯首听命,如约来到了电视节目中。更有甚者,警方还在采取预防措施,生怕他突然之间向哪辆校车发泄怒气。并且,警方还是没有任何办法找到他。
然而,他还要继续显山露水。11月初,他寄了两个包裹给《旧金山新闻报》,其中包括一张明信片(“我是黄道十二宫”)、另外一封密码信、一封七页的信,以及他宣称将用来炸校车的一颗炸弹的手绘示意图。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还将从保罗·斯代因的血迹斑斑的衬衫上撕下来的另一块布装在了另一个信封中,尽管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笔迹、包括他总是多贴邮票的奇特习惯,都已经为警方所熟悉了。实际上,他只能多贴邮票,这样他可以将这些信封随手扔到随便哪个邮筒中,不必和任何邮政工作人员接触,以免以后工作人员能够认出他来;并且他知道这样的话,他的信肯定是能够寄出去的。以后我们会看到有个大学航空炸弹怪客用的也是同样的策略。
尽管人们非常注意黄道十二宫手绘的炸弹,但是我认为这两封信中的其他方面,特别是那封长达七页的信,更加值得注意。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段话:
……我已经变得非常生气了,因为警方说了许多有关我的谎话。因此我将会改变我收集奴隶的方式。我不再会向任何人宣布我犯下的任何罪行,这些罪行看起来应当像普通的抢劫、杀人、伪造的交通事故,等等……
在后来寄出的许多封信中,黄道十二宫会提到他采用的经改进的新的死亡人数统计方法。每收到一封信,警方都会重新分析处在他们各自辖区内的未侦破的谋杀案件,看看这些案件之间是否会有什么关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有些人曾认为黄道十二宫和“铁路杀人犯”就是同一个人。但是当1988年大卫·卡彭特被判犯下那些凶杀行为之后,此种说法又不攻自破了。当大卫·卡彭特还在狱中服刑的时候,又发生了几起黄道十二宫谋杀案。现在大约有五十多个被害人是黄道十二宫的牺牲品,当然,这个数目取决于你问的人是谁。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不懂得将案件联系起来的反面:将案件过分联系起来;每当出现一个未破获的大型系列案件时,此种情况都会发生。直到今天,人们还认为其中某些案件是西雅图的“绿河杀手”所为,尽管绿河杀手连环谋杀案中的第一宗实际发生在1982年1月。
黄道十二宫连环谋杀案至今仍然困扰我们的原因之一是:黄道十二宫同时抓住了精神变态者和守法者的想象力,他不仅成了旧金山湾区的罪犯争相模仿的对象,而且多年以后还为纽约和东京的罪犯所效仿。出于某些不便在这里说明的复杂原因,警方立即就知道这些案件根本不是黄道十二宫所为。
黄道十二宫成功地做到的一点是,他使人们有这样一种错觉:不论他是否真的在杀人,人们总是认为他肯定还会继续作案。只要他写信宣称某宗案件是他干的,围绕他的种种传说马上又开始繁荣昌盛起来。他责备警方,说他们的谎言迫使他对自己以后犯下的特定犯罪行为保密。如果他再也不杀人了,人们还会继续怀疑某某案是不是他的作为。而如果他继续作案的话,他已经不再向警方提供任何能泄露他身份的线索了,因此他就能很好地保护自己。实际上,自此之后,他再也不寄什么被害人的衬衫碎片了,并且再也不像在简森/法拉第案和费琳/马高案中那样描述犯罪的具体细节了。
黄道十二宫系列谋杀案中最大的一个谜是:他为什么金盆洗手了。他到底身在何方?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说得很明白,连环杀人犯是不会做诸如搬到南方去然后就歇手不干这样的事情的。由于斯代因谋杀案发生之后的许多年中,黄道十二宫还是不断往外界写信,我们知道他没有死,或者说,他没有被关押起来。可能他生病了或身体恶化了,因此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作案了。但是我认为他只是害怕了。当你刚刚杀死一个人,身上还满是血迹,而且肾上腺还在不断涌动,之后不久就遇到了两个警官,这可不是什么你很快就能忘得一干二净的事情。
从他犯下的罪行、寄出来的信件以及他能够成功逃脱警方的身份甄别和抓捕来看,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早就看到了不祥之兆。像他这样的罪犯是不可能轻易罢手的。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是不大可能放下那种多年以来断断续续地总是出现在报纸头条新闻中,引发无数人对自己万分恐惧的高度快感,主动放弃所有力量和对他人的控制力并主动投身监狱的。我认为这个时候警方就应当二十四小时注意自杀方面的情况。我在“大学航空炸弹怪客”西奥多·卡辛斯基案中就是这样建议的。
同时,我认为黄道十二宫对自己被人认为处在弱势地位非常不满。他不会承认此种恐惧感,因为这只会让他感觉更加卑微。因此,相反,他在一封又一封信中四处出击。他不仅表现得愤怒不已,而且必须通过说明能证明他在智力上优越地位的无数作案细节,来强烈弥补他的卑微感。
警方永远不会抓住我,因为对他们来说,我绝顶聪明。1. 我只有在作案的时候才看起来像人们描述的样子,在其他时间之中,我看起来完全不同……2. 迄今为止我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与警方所说恰恰相反……我戴着透明的指尖保护装置。实际上我是将飞机用胶合剂涂在两只手的手指尖上——几乎不露痕迹,但是非常有效……如果你们对我为什么擦那辆出租车感到奇怪的话,我实际上是要留下假线索,好让警方跑遍整个城市……我喜欢整治蓝制服的猪。嘿,蓝制服猪,我在公园中——你们在用救火车来掩饰你们的巡逻车呼啸来去的声音……补充一下。那两个警察简直就是傻瓜,当时我离开那辆出租车已经三分钟了。我正从山坡上走下来到公园中去,这时那辆警车停下来了,其中一个警察叫我过去,问我是否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我说是的,我看见一个男子,手中还拿着手枪往那边跑了,那两个警察就突然加大油门,在拐角处转了个弯。我叫他们这样做的,之后我就消失在公园里……嘿,猪们,难道你们不会因为自己犯下的各种错误而后悔不已么?
就像“山姆之子”一样,大卫·伯科维茨也写了很长的信寄给警方,并且最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精神状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了。
12月,黄道十二宫寄来了另外一封信,里面附了保罗·斯代因的另一块衬衫碎片,这次他是把信寄给了梅尔文·贝利。这次他把自己的话写在了一张圣诞节贺卡上,并且语调也和上次那种谩骂攻击完全不同了。他开始祝梅尔文“圣诞节快乐”,然后就说希望获得帮助,并表达了某种不安全感。
亲爱的梅尔文:我是黄道十二宫。先祝你圣诞节快乐。我请你为我做的一件事情是求你帮帮我。我无法寻求别人的帮助,因为我里面的这个东西不让我这样做……
黄道十二宫警告说,若没有获得帮助的话,他可能杀死他的“第九个甚至第十个被害人”,暗示在保罗·斯代因谋杀案之后他还在计划更多的谋杀案,尽管他没有提供任何细节。然后他强调“请帮帮我,我要淹死了”,还有“请帮帮我,我很快就要控制不住了”。
梅尔文·贝利对这封信表示了乐观。他公开宣称,这封信表明黄道十二宫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被抓住之后,已经打算自首了,并且希望梅尔文能够帮助他逃过死刑、毒气室。梅尔文·贝利甚至宣称有个自称是黄道十二宫的人打电话到他家中,但是他碰巧不在家里,因此那个人就和管家好好地聊了一顿。梅尔文说,他认为当他哪天回家时,很可能会发现他们俩又在聊个不停呢。
多年以后,我已经过世的同事和亲密朋友穆雷·麦伦对这封信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穆雷认为,这封信表明黄道十二宫陷入了抑郁之中。穆雷认为当不断袭来的抑郁情绪占据了这样一个罪犯的整个身心时,“在此种恶性抑郁情绪的某个阶段,他终于自杀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我认为黄道十二宫最后可能确实自杀了,但是我同样相信,即使在此种抑郁情绪之下,他写那些信,还是为了操纵、支配和控制收信人;并且他知道,他可以以此操纵、支配和控制他们会接触到的更大范围内的人。因此,当这个无名罪犯确实在圣诞节期间感觉越来越孤单、越来越被社会所抛弃时,我认为他写这封信是为了玩玩公众的同情心:此前他还没试过从公众那里得到同情心呢。为了支持我的判断,我在这里要指出,尽管梅尔文·贝利一再保证他会确保黄道十二宫逃开死刑、毒气室,并且竭尽全力帮助他,但是那个杀人犯还是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了。
正如我早些时候曾指出的,当你在分析此种类型的罪犯时,你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有许多案件看起来似乎都是黄道十二宫做的。由于我们面对的这个罪犯几乎总是在杀害陌生人,不断在各地流窜,并在不同犯罪中使用不同的武器和作案手法,因此我们可能在实际上凶手并非他的案件中逗留了过长的时间。同时,我们又得避免犯下没有将相关案件相互联系起来考虑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