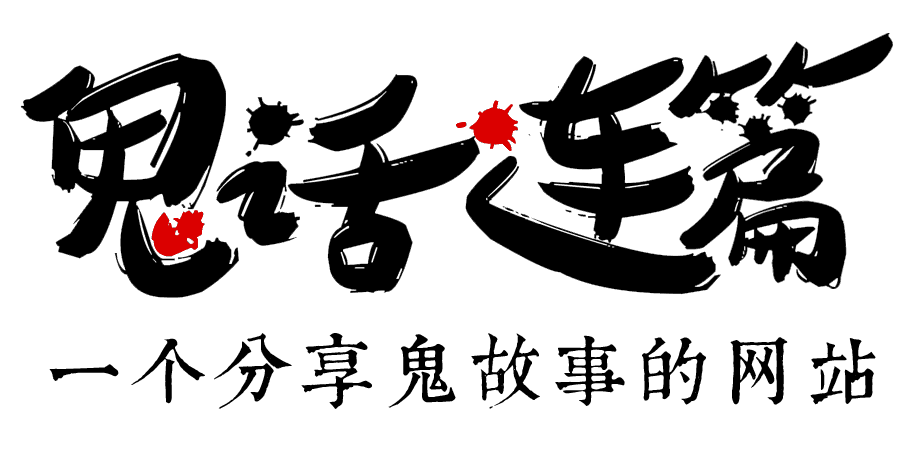达琳·费琳是一个喜爱社交活动的年轻女郎,二十二岁,和丈夫迪安还有他们年幼的女儿蒂娜一起居住在瓦列霍市。抽水站附近的这宗谋杀案发生之后不久,她告诉她在特里酒店的一个同事,她认识(至少是知道)这两个被杀害的年轻人,因为她曾经到侯根中学上过学,而这所中学和贝蒂·劳·简森家只隔了一个街区。达琳觉得他们俩被谋杀的事情是如此令人恐怖,她再也不愿意到这片地区来了。
简森/法拉第谋杀案发生六个月后,7月4日国庆节那天,达琳打电话给她的朋友麦克·马高,问他晚上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出去。接下来,达琳把蒂娜交给两个保姆之后,就到迪安工作的那家意大利酒店(和达琳工作的酒店不是同一家),告诉迪安说她和妹妹克里斯蒂娜要去梅尔岛附近看船舶展览。迪安告诉她,他邀请了几个同事下班之后到家里聚会,让她回家时顺便买一些烟花回来。接着,在去看展览之前,她和克里斯蒂娜先到特里酒店邀请了一些朋友晚上到家里聚会。她又给麦克·马高打了电话。看过展览之后,她们俩回到了迪安工作的酒店。这个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十点了。达琳打电话问了问女儿的情况。保姆告诉她特里酒店有个人在找她,于是她就回到了特里酒店。接着,在开车送克里斯蒂娜回家之后,达琳就开车回到家中。
本来她打算在送两个保姆回家之后,清理一下屋子为聚会做好准备。但她接到一个电话,就问那两个做保姆的女孩,她们是否愿意再在家中呆一会儿,她出去买些烟花回来。她们说愿意。于是达琳就开车到了麦克·马高家。马高当时正在家中很焦急地等她,他没关电视和电灯就跑出来了,并且门也没有关。当他们离开马高家时,马上意识到被另外一辆汽车跟踪了,那辆汽车颜色浅亮。他们试图甩掉它,最后冲到了哥伦布公园大道上,这条路是往城外去的。他们转到了蓝岩泉高尔夫球场,这个地方不像赫尔曼湖滨路那里的抽水站那样隐蔽,但是人们都知道这也是片情人们幽会的地方。达琳开车进停车场后就将那辆雪佛兰熄火了,这时后面那辆车开过来了。那辆车在那里急停之后马上就疯了一般地冲走了,但是几分钟之后又回来了。麦克后来回忆说,那辆车就像警车那样停在他们的车后,堵住了他们的退路,并且打开车灯照着达琳的车。他所知道的下一件事情就是,他听到什么东西打在车窗户上,然后在他被击中时,他看到一束亮光在他眼前闪过。子弹不停地射过来。达琳已经倒在方向盘上,中了九弹:两个胳膊各中了两弹,背部中了五弹,击中了肺部和心脏。
麦克想逃走,但是没有发现车门把手。当他正在努力挣扎时,看到那个枪击犯回到了自己车中。这个男子曾经转过脸来,麦克把他看清楚了:那个人大约快三十岁,矮壮结实,体重大约有二百磅,五英尺八英寸高,浅棕色卷发,平头。他穿着海军士兵穿的那种风衣,裤子皱皱巴巴,挺着微微外凸的肚子。麦克以为枪击犯走远了,于是因为忍不住痛就喊了一声,这时那个男子马上就改变车向,回到达琳的汽车那里。当麦克没命地跳到车后座时,他向麦克补了两枪。接着他又朝达琳开了两枪,然后就回自己的汽车中扬长而去。
麦克从里面将手伸到车窗外把车门打开,从汽车上滚了下来。他的脸、脖子、右臂和左腿都在流血。其中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颚骨和舌头,他甚至没有办法喊出来。幸运的是,有三个年轻人晚上出来找他们的另一个朋友。他们开车到了停车场,发现了趴在地上痛苦扭动的马高。他们立即跑开去找人来帮忙。
大约午夜刚过十分钟的时候,瓦列霍警察局的总机响了。两个警员首先到达现场,之后不久探长约翰·林奇和警官艾德·拉斯特也到达现场。现场触目惊心:麦克·马高浑身是血,痛苦不堪;而达琳则趴在方向盘上,奄奄一息。林奇说达琳当时想对他们讲些什么,但是他们听不清楚。实际上,此前林奇和拉斯特已经得到报案,报案人说他听到枪击声。报案人是高尔夫球场管理员的儿子,他听到枪声还有一辆汽车疾驰而去的声音。但是当时是国庆节,因此他们俩认为那肯定是烟花爆竹发出的声音。根据极全面的《黄道十二宫》一书的作者、记者罗伯特·格莱史密斯的说法,林奇和拉斯特极端后悔,说如果他们反应更加迅速的话,他们可能会在嫌疑犯开车逃离现场时遇到他。更让他们后悔的是,当他们到达现场时,发现认识其中一个被害人。达琳在自己工作的酒店中认识了许多警官,甚至她还和其中一些人约会过。并且她和迪安就住在瓦列霍治安办公室隔壁。凌晨零点三十分,警方宣布,达琳在送到凯泽基金医院时就已经死亡了。麦克·马高伤情严重,下巴、右臂、左腿都需要手术,但他还是能够完全恢复的。
在犯罪现场,警探们发现达琳的雪佛兰车两边的车窗都开着,发动机也还在运转。汽车还停留在低速挡,收音机还响着,达琳没有挂停车挡。所有这些都与麦克·马高的描述相吻合:汽车当时停了下来,还没等达琳熄火或再次开动汽车,罪犯就已经冲上来了。
血迹斑斑的汽车内,除了达琳和麦克的钱包之外,警方还发现了口径为九毫米的弹壳。马高没有提到罪犯曾经停下来重新上子弹,并且罪犯至少射击了九次,因此罪犯所使用的肯定是一把布朗宁半自动枪。
把发生在两英里之外的赫尔曼湖滨路上的谋杀案和这个谋杀案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两个案件中,罪犯都是在晚上袭击坐在停靠在偏僻地点的汽车中的年轻情侣,罪犯用的都是枪。但是在这个案件中,根据劫后余生的麦克的说法,罪犯当时是大力追赶达琳的车,几乎就是这种追赶迫使达琳开车到达犯罪现场的。并且,这个案件中,被害人情况的相关线索表明,这可能不是一个陌生人谋杀案,因此可能更容易查明罪犯的作案动机。
警方对达琳·费琳的背景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达琳·费琳可能并不是罪犯偶然遭遇的什么作案目标。根据朋友们和同事们的说法,达琳喜欢出去,并且经常和不是她丈夫的男子呆在一起,例如麦克·马高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对此迪安似乎倒不像他的朋友们那样在意。每次他们对他提及这事时,他都为妻子辩解,提醒他们说妻子现在还年轻,还不喜欢受拘束。他坚持认为,妻子出去不过纯粹是为了找乐子罢了,她并没有和其他人发生什么风流韵事。(当然这可是1969年的加利福尼亚。)此外,迪安当晚根本就不在现场:他当时和同事们在一起。
但是,警方还需要对达琳生活中的其他男子进行调查,这包括她的第一任丈夫吉姆。吉姆有枪。据称,达琳很害怕他。但是他和那天晚上那个枪击犯的外貌特征不符,因此警方就认定他不是作案嫌疑人。另外一个人——据称这个人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追求达琳——也被警方排除在外了,因为警方发现案发之时他和妻子一起呆在家中。
有些目击证人说他们曾经看到另外一个男子,坐在停放在达琳家前面的一辆白色美利坚牌汽车里,暗中监视达琳。其中一个保姆说,当时她曾经告诉达琳她看到那个男子坐在汽车中监视她,达琳则回答说她曾看到过那个人杀人。达琳的姐姐帕姆也说看到一个开着白色汽车的男子把几个神秘包裹送到她家中,那个男子警告帕姆不要打开其中一个包裹。她曾多次看到这个男子,她说他是一个黑头发的、穿着体面的人。有时候他还戴角质架眼镜。
达琳的另外一个姐姐琳达也看到过这个男子出现在达琳家附近。当时达琳要举办一次聚会,他过来把要举行聚会的地方油漆了一通。据琳达称,达琳曾告诉她离这个男子远点。保姆和达琳的两个姐妹都说,达琳似乎很害怕这个男子。达琳被杀害的那个晚上,她曾经在特里酒店的停车场和一个开白色汽车的男子发生了激烈争吵,当时的情景被妹妹克里斯蒂娜看到了。
大约在6月底的时候,也就是在达琳被杀害前不久,达琳向克里斯蒂娜预言说,有件什么大事马上就要发生。达琳无法说或不愿再对她细说什么,但是她说这件事肯定会上报纸的。熟悉达琳的人说,她和第一任丈夫到维京群岛度蜜月时,他们可能碰到了一群匪徒。难道在那里时她曾看到或听到了某个谋杀案?是不是涉及毒品呢?但是最终,所有这些猜测都没能够对确认杀害她的凶手有任何帮助。
麦克·马高也是个值得注意的人。他和达琳是在特里酒店相识的,他当时和双胞胎兄弟大卫一起在那里工作。这对19岁的双胞胎为达琳争风吃醋,争相讨好达琳,希望赢得她的青睐。国庆节那天,麦克穿了好几件衣服,这可让警方不得其解。后来他向探长林奇解释说,因为他对自己的瘦小身材特别敏感,所以就希望以多穿衣服来掩盖自己的不足。根据曾经和罗伯特·格莱史密斯交谈过的几个人的说法,当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况下问他当晚的情形到底如何时,他所说的也就有所不同了。不同的地方包括:他们是如何到达蓝岩泉高尔夫球场的——他们是突然被凶手追赶,还是他们先遇到了那个曾经和达琳争吵的男子,然后被那个男子追赶到停车场的;凶手的外貌特征和他开的汽车,等等诸如此类。达琳的姐姐帕姆认为,麦克认为达琳认识那个凶手,麦克这样做只不过是出于对她的爱而尽力保护她。总之,康复之后,麦克就搬走了。
7月5日凌晨零点四十分,瓦列霍警察局的总机响了。一个男子告诉接线员南希·斯洛甫说,发生了一起双重谋杀案。他详细描述了如何能到达现场,南希认为他要么是事先排练过,要么就是照着稿子念的。他不允许她提问打断他的话,一直不停地说到最后。为了让她相信他就是凶手,他不仅详细描述了犯罪现场所在的地点,而且还告诉她说,他是用一把九毫米的鲁格尔手枪把那两个人杀死的。然后他还宣称“去年死的那两个孩子”也是他杀的,接着说了声再见就把电话挂了。
我毫不怀疑,那个打电话的男子是照着稿子念的。他是一个高度条理型的罪犯。他知道警方可以追踪他的电话,他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让警方相信他就是凶手并且把他的话说完,之后马上就得把电话挂了。如果警方能在枪杀案发生之后不久就确定嫌疑人的话,我会建议他们把打电话的男子说过的话记录在搜查证上——现在我们在敲诈或绑架案件中就经常这样做。
几分钟之后,太平洋电话公司查出这个电话是从瓦列霍治安办公室和达琳家附近的一个加油站前面的投币式公用电话打过来的。当时经过那个电话亭的目击证人称,他看到里面有一个矮壮的男子在打电话,这个男子的外貌和麦克·马高对那天的枪击犯的描述很吻合。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大约凌晨一点三十分,达琳家、迪安·费琳弟弟家、迪安的父母家都接到了很“古怪”的电话。每个电话中,打电话的人什么都不说,他们只是听到那个人的呼吸声。
这些电话,以及凶手打来电话报告他杰作的那个投币电话亭所在的位置都表明,这个无名罪犯至少认识最近被他杀害的人中的一个。首先,打电话的时候,发生枪击案的新闻以及被害人的身份都还没有公开发表。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许多罪犯都一边盯着他们杀害的人的家里,一边打电话报告他们自己的罪行,然后在一旁等着看热闹,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但是,在谋杀案发生之前几个月,达琳和迪安才住进靠近治安办公室隔壁的房子。电话簿中的地址是他们的老地址。如果这个罪犯选择那个电话亭的目的确实是为了从观看他的杰作中得到满足,那么他不但要知道达琳的名字,而且要对达琳的生活比较熟悉,能够知道她最近不久刚刚搬过家。
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那个达琳害怕的、开着白色汽车的神秘男子呢?当然,以下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罪犯根本就不知道他杀死的人是哪根葱,选择靠近治安办公室的电话亭打电话只不过是为了嘲笑警方罢了。
但是,如果要抓住罪犯和这些被害人之间的联系,必须将达琳作为重点突破口,这是很有道理的。除了被害人情况之外,犯罪现场本身也让我们知道,她是罪犯发泄愤怒的主要对象。她承受了罪犯的主要火力,比起她的同伴,她身上的枪伤更多而且更严重。本来此种性质的案件中,男子,作为对罪犯有更大威胁的人,应当受伤更加严重才对。此外,由于枪击犯是在马高那边向汽车射击的,因此达琳本来应该更可能活下来才对。
但是即使假定罪犯不认识他杀害的对象,他集中射击女被害人也同样是可以说得通的。纽约发生的“山姆之子”系列案件中,罪犯大卫·伯科维茨就有意靠近汽车中女士所在的那一边,然后用他的四十四毫米马格南左轮手枪朝她们射击。她们的男性同伴是次要目标。
根据马高的说法,在离开之前,罪犯往后退了退,接着又向他们射击了多次。考虑到马高当时已经受伤而且身体虚弱,我们认为罪犯这样做本应该是要让马高彻底死亡的。但是相反,他射击了四次,有两次是向达琳·费琳射击的,尽管他已经看到她受的伤足以置她于死地了。他不仅让马高活着,还让马高能够看清楚他的外貌。
达琳谋杀案发生之后不到一个月,那个自称是凶手的人又开始和外界联系了,但是这次是和媒体而不是和警方联系,而且是通过信件的方式。《旧金山新闻报》、《旧金山监督报》和《瓦列霍时代先驱报》都收到了一个自称就是那个连环杀手的人寄来的几乎一模一样的信。写给《旧金山新闻报》的那封信的开头是这样的:
亲爱的编辑:
我就是去年圣诞节在赫尔曼湖滨路杀死那两个年轻人以及今年国庆节在瓦列霍的那个高尔夫球场杀死那位女士的人。为了证明他们确实是我杀的,我会在这里说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我和警方才知道……
这些信件接下来详细描述了两宗案件的细节,包括他使用的子弹和被害人尸体的位置。每封信中还附有一部分很长的复杂的密码信:是由写得很工整的符号构成的。每家报纸收到的都只是这封密码信的三分之一。根据这些信件中的说法,如果这封密码信得到破解的话,它就会泄露罪犯的身份。
我基本上不认为大多数执法人员会相信罪犯所说的只要破解了密码信就能查明他身份的鬼话。但我强调,当罪犯开始和我们联络时,那就是个好兆头。想想“大学航空炸弹怪客”案,我们几乎也是毫无头绪。在这样的案件里,我们从罪犯写来的信件中所得到的行为线索,比从犯罪现场得到的行为线索要多得多。
当罪犯开始和外界联络时,这就是开始抓捕他的最好时机。他的傲慢感和强大感会让他更多地泄露自己,这让我们获得了让公众中的某个人指认他的很好手段(就像我们在“大学航空炸弹怪客”西奥多·卡辛斯基爆炸案中所做的那样),并且这也让我们能够领悟他的动机,这样就可以设计出更好的心理策略,引蛇出洞。当我们发现了诸如贪婪、愤怒或复仇这样的传统动机都不适用的一系列案件时,收到罪犯寄来的信件对于我们获悉他的动机来说简直就是无价的。
这个案件中,罪犯不仅要用他的密码信来证明他就是真正的凶手,并以此来嘲笑警方;而且,对他来说,警方知道他就是真凶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所有当地报纸的每一个读者都知道他,并且害怕他。
我希望你们能将这封密码信发表在你们的报纸头版上……如果你们不在1969年8月1日星期五下午之前发表这封密码信的话,我会在星期五晚上继续疯狂地杀人。我会在整个周末都到处游荡,在夜间杀死落单的人一直到我在周末杀死十二个人为止。
这几家报纸和警方合作,只发表了这些信件的部分内容,而没有全文发表。正如他们进行的调查工作的其他方面一样,当局希望对某些事情保密,这样还会有一些细节只有罪犯和警方才知道。对罪犯而言,如果他知道这些细节的话,他就能够在以后的信件中进一步证明自己就是警方要找的真凶。对警方而言,最好的情况是,这些细节可以是以后辨认和指控罪犯的基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那些密码后来并没有像罪犯所明确宣称的那样会透露他的身份,但是这封密码信却提供了一些极有价值的线索,这可能是罪犯所始料不及的。首先,罪犯不嫌麻烦地把这样的东西写出来,那么我们就知道罪犯不是那种普通的莽撞的杀人犯。这个人不仅非常细心,不仅对自己具有比警方更高的智慧极端自豪(弥补他在生活中所感觉到的卑微),而且他还喜欢这些极端需要注意细节的活动。请想一想,要写出那些密码符号,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同时还得努力掩藏自己通常的书写习惯!只要有一笔写错,就得全部重来。这几乎需要制造炸弹者所具有的那种耐心。
并且,我们手头还掌握了那些符号。当地报纸的普通读者可能不熟悉这封密码信中的大部分符号,它们包括气象学和占星学符号、摩尔斯电码和海军信号码以及很多希腊文符号。我们面对的这个人,如果说没有获得某些高度专业领域的训练的话,也至少是和此种领域有某种程度的接触,即使他对这些领域并不十分精通,也需要带这些符号的相关参考书籍。尽管我们认为这个无名罪犯可能是个离群索居的人,但是除了他喜爱独处之外,他的家人或朋友应当知道他还受过相关教育或者有相关工作背景。
就像那个炸弹怪客一样,这个罪犯可能认为这些信件和密码,就像他所进行的谋杀一样,全都是他的艺术杰作。我们认为他有一个单独的工作地点,在那里他可以仔细地写出这些密码,那里也收藏着他的参考资料:有关密码、解码和符号的书籍,以及报道他的罪行和信件的报纸。这个地方不大会是一个锁起来的车库或者有时会冒烟气或发出奇怪声音的某个地下室房间,而是一个神圣的、井井有条的工作空间,这个罪犯会极端保护这个所在。
让我们将这些性格特征和前面提到的一个犯罪具体联系起来看一看。不论推定达琳认识还是不认识那个杀人犯,谋杀她的肯定不会是一个想成为她的情人但被拒绝后发怒的人,也不会是某个想掩藏他以前犯下的罪行的人。真正的凶手实际上是在玩一种恐怖的智力游戏,他的目标针对的远远不止是某个具体的个人。
因此,如下这种情况看起来就很合理了:尽管警方从海军情报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以及联邦调查局请来了许多专家来帮忙,但是最终破译这些密码的却是一对喜爱读报的、热爱公益的夫妇。这些报纸将这封密码信的不同部分刊登在不同日子出版的报纸上,到了8月3日星期天,所有三个部分都已经向公众公开了。
唐纳德·金·哈登,四十一岁,中学历史和经济学教师,还有他的妻子贝蒂耶·琼花了好几天终于破解了这封密码信。警方所请的所有专家都认同了他们的工作成果:
我喜欢杀人, I LIKE KILLING PEOPLE
因为杀人是 BECAUSE IT IS SO MUCH
如此有趣,它比 FUN IT IS MORE FUN THAN
在森林中打野味 KILLING WILD GAME IN
还更有趣,因为 THE FOREST BECAUSE
人是所有动物中 MAN IS THE MOST DANGEROUE
最危险的动物。 ANAMAL OF ALL TO KILL
杀人让我获得了 SOMETHING GIVES ME THE
最刺激的体验, MOST THRILLING EXPERENCE
这种体验甚至比和一个姑娘 IT IS EVEN BETTER THAN GETTING
疯狂做爱达到性高潮还要刺激。YOUR ROCKS OFF WITH A GIRL
杀人的最大好处是, THE BEST PART OF IT IS THAE
当我死的时候,我会在天堂中 WHEN I DIE I WILL BE REBORN
获得再生,而那些我杀死的人 IN PARADICE AND THEI HAVE
会成为我的奴隶。 KILLED WILL BECOME MY SLAVES
我不会告诉你们我的名字, I WILL NOT GIVE YOU MY NAME
因为你们会想方设法 BECAUSE YOU WILL TRY TO SLOI
减少或夺走我为我死后的生活所DOWN OR ATOP MY COLLECTIOG OF
收藏的奴隶 SLAVES FOR AFTERLIFE
EBEORIETEMETHHPITI EBEORIETEMETHHPITI
破译出来的文字只是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凶手的狡猾而已。例如,在密码专家分析这些密码时,他们试图运用某些基本的规则。这封信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字母“e”。为了隐蔽他的踪迹,制作这封密码信的罪犯使用了七个符号来代表字母“e”。只要你读一读这封已经破解出来的密码信,你就会发现许多拼写错误。但是,到底哪些是罪犯真正的拼写错误、哪些又是罪犯故意拼错的,这似乎并不清楚。
在分析这封信的过程当中,专家们经常只注意罪犯所说的,他在“天堂”中获得再生之后,他杀死的人将会成为他任意使唤的奴隶。但是在我看来,罪犯所提到的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危险的动物”,若综合考虑这封密码信的其他部分的话,更能反映出罪犯的宗教式的信念。这就好像理查德·康内尔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危险的游戏》一样,在这个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的短篇小说中,讲述了一个住在自己的小岛上的富有的疯子,通过架设假的航灯,诱惑过往的水手驾船到靠近他小岛的很危险的暗礁那里去。接下来他就将他们救起来,放了他们,然后就在他那巨大的房子中像追捕野兽一样追捕他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里面对的这个连环杀手是一个文学天才或者格外博学,因为当时许多中学要求学生阅读的作品中都包括了这部192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这也不意味着这个杀手看过由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某部电影。但是,当考虑到这封信的其他部分显得很是笨拙时,我们就可以说,他用了这样的句子应当不只是纯属巧合。我认为这至少说明他接受了相当不错的教育。我还认为,当罪犯说杀人比“和一个姑娘疯狂做爱达到性高潮还要刺激”时,他说的是他内心的大实话,因为我不认为他真正有过什么欲仙欲死的性体验。正如我们此前提到的,与女人有成功的、充实的关系的男人,一般都不会枪杀女性。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收到这些信件的那个星期的周末,罪犯并没有大肆杀人,尽管《旧金山监督报》并没有按罪犯要求的在星期五之前发表寄给它的那部分密码信,而是在星期天才将它发表出来。在我看来这毫不奇怪。上面提到的那个大学航空炸弹怪客也威胁说要在假日的一个周末在洛杉矶外炸毁一架班机。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大肆享受着由他的威胁所引发的关注和恐惧。对我们面对的这个罪犯而言,比和一个姑娘做爱达到性高潮还要更好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幸灾乐祸地看着公众、警方和媒体坐立不安,等待他做些什么事情。他无法追求到的每个女孩都知道他发出的威胁,而所有已得到自己心上女孩的男子也都听到了有关他的新闻;整个周末,全国的警力都在努力破解他的密码信,这对他来说十分刺激,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力量。
最后,还有一个密码信最后一行到底是指什么的问题。当破解结果被公布时,公众都试图从最后这一行破解出罪犯的名字。警方也密切注意公众提出来的名字,但是读者们也可以想象得到,警方毫无收获。
同时,瓦列霍市警察局长杰克·E·斯蒂尔茨还公开表示,他甚至怀疑这些信件和密码不是真正的罪犯寄来的。尽管其中包括一些没有公开的有关谋杀案的信息,但某个看到过犯罪现场的人也是能够写出这些东西来的。斯蒂尔茨公开要求无名罪犯再寄一封信来,信中必须说明更多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细节。斯蒂尔茨的要求马上就得到了满足。警方得到的可不只是一封信而已,而且得到了可以算得上是罪犯的身份标识的东西:罪犯给自己取了个名字——黄道十二宫。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地区,这个名字不久就成了恐怖的代名词。尽管这个名字是如此的“性感”和具有诱惑力,罪犯对他为什么选择这个名字没有作出哪怕一点点的解释。有人认为这可能意味着罪犯和占星业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但是罪犯后来写来的那些信中没有什么东西证明这种推断是令人信服的,尽管罗伯特·格莱史密斯从中发现了一份可追溯到十三世纪的“黄道十二宫图符”。这个二十世纪的“黄道十二宫”可能是将这份黄道十二宫图符中的某些符号直接用在了他的密码信中,或者是对它们做了一定改动。
斯蒂尔茨提出要求的第二天,这封三页的信就寄到了《瓦列霍时代先驱报》。它是这样开始的:
亲爱的编辑: Dear Editor
我是黄道十二宫。 This is the Zodiac speaking.
在回答你们提出的 In answer to your asking for
要我提供我在瓦列霍愉快生活中的 more details about the good
更多细节的要求时, times I have had in Vallejo,
我还非常愿意 I shall be very happy to
提供比你们要求的更多的资料。 Supply even more material.
另外,警方 By the way,are the police
是否在破解密码上 having a good time with the
感到愉快顺手呢 ……code...?
以此种古怪的、半帮忙式的口气来写信,这说明罪犯对他能够愚弄警方感到异常高兴。许多人将黄道十二宫嘲笑警方的信件和开膛手杰克的“亲爱的老板”等信件相比,尽管在第一章中,我已经说明我认为那些信件是伪造的。然而,我们还是不能排除此种可能性:这个罪犯是从白教堂连环谋杀案的凶手那里得到了启发。我们要记住,罪犯此前曾在他的密码信中提到过一个经典的短篇小说;照这样说来,罪犯曾经研读过白教堂连环谋杀案是再自然不过了。无论如何,他认为自己胜出警方和媒体一筹,就像写“亲爱的老板”等信件的伦敦东区谋杀犯希望我们认为的一样。
黄道十二宫接着清楚地写出了他谋杀达琳·费琳以及试图谋杀麦克·马高的一步一步的详细细节。很明显,下面这些描述能够向警察局长斯蒂尔茨证明写那些信件的人就是凶手本人无疑。
在国庆节……那个男孩开始坐在汽车前排的座位上,我开始射击了。当我将第一颗子弹射向他的头部时,他几乎同时就跃向汽车后座,因此我没有打中他。他落在后座上时,后面的车门猛然打开,他的腿露出来了,因此我能够去射中他的膝盖……
他甚至描述了当他在打电话时那个经过电话亭的目击证人,他说自己“想和警察逗着玩儿”,因此这至少证明那个电话确实就是他打给警方的。黄道十二宫还详细描述了他是如何谋杀简森和法拉第的。
去年圣诞节,在那次谋杀案中警方感到奇怪,那样的黑暗中我为什么能够射中他们?警方没有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当警方说当晚照明很好,而且我应当能够看清楚他们映在地平线上的轮廓时,就露怯了。简直一派胡言。那个地方被高坡和树木环绕。我的方法是把一个很小的三角形闪光灯装在我的枪管上……装好之后,子弹会精确地击中闪光中心的那个黑点。我所要做的只不过就是尽情射击罢了……
这样一来罪犯就不仅证明他在简森和法拉第被杀的当晚确实在现场,而且他还积极追踪着媒体对他的报道。现在你们大约明白了我为什么说媒体报道事实的方式会对罪犯有影响了吧。在这个案件中,好几个月以来,黄道十二宫肯定被警方把他杀死被害人说得很容易感到气恼不已。这种说法更加加剧了他的沮丧感和卑微感:他被误解了,他的高超技巧也被低估了。他必须确保他的作案计划、思想和技巧能够被人充分了解。因此,这么多个月过后,他还认为有必要将这些信息写在一封回答警方就他最近犯下的罪行提出疑问的信中。这又一次证明他有自觉的强迫心理。这还告诉我们,在与他人的交谈中,他可能抱怨过警方和媒体对他以前的谋杀行为的报道。我可以想象,在圣诞节期间杀人之后的几天中,他向自己的知己之交(也是个孤僻之人,不及他聪明,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心腹之一)抱怨警方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胡说些什么。例如,他可能说,你们这帮家伙睁开眼睛看看,当天晚上是多么黑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