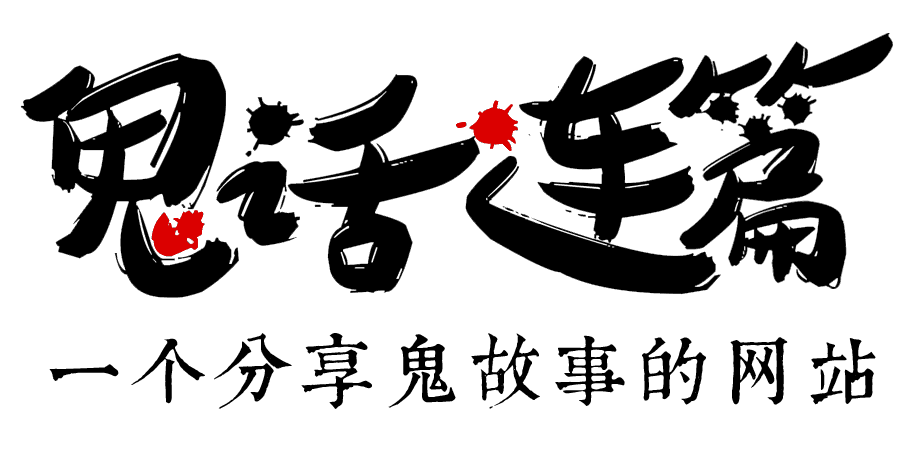约翰·F·康登,时年七十二岁,胡须花白,几乎总是穿着干净利落的黑色衬衫和黑色西服,是布朗克斯地区一所学校已经退休的物理教师兼校长。他认为布朗克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尽管大家都称他为“博士(Doctor)”(1),但我们没有发现他获得了哪个专业的博士学位,而且他显然也不是什么医生。吉姆·菲舍,我早年在联邦调查局时他是那里的特警,现在则是教授兼作家。在他很重要的一本书《林德伯格案》中曾提到,康登自称为学者。从康登后来和警方以及媒体打交道的行为来看,我推测康登一定是这样一位教师:喜欢站在教室前面自言自语;他可能对帽子掉在地上都大肆评论一番;他也极端爱国,爱得有些矫揉造作;他为这起针对美国最伟大的英雄的犯罪而感到震惊,认为这是国家的耻辱,希望自己能帮上什么忙。我认为,同样可能的是,他还想通过这个将要成为历史上最轰动性的事件获得某种个人关系并满足他自己的妄自尊大。
当读到斯皮太尔和比茨这两个卑劣的黑社会暴徒正在充当中间人的消息之后,康登写了一封信给《布朗克斯家庭新闻报》。这封信发表在该报3月8日那一期上。这封信中,康登提出自己来充当林德伯格和绑架犯之间的中间人,并且愿意另外投入自己辛苦挣来的一千美元,作为给绑架犯额外的赎金。我认为,从这件事上,康登的自以为是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由于这份报纸在布朗克斯区之外几乎是默默无闻,调查人员中没有人重视康登的提议,如果说他们确实知道他的提议的话。当然林德伯格也没有。
信在报纸上发表之后,康登出去了,直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回到家中。回到家时,按照习惯,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那天的邮件。其中一个信封上的笔迹粗糙潦草,在里面有一份手写信件:
亲爱的先生:如果你愿意担当林德伯格案件中的中间人,请严格按照我们的话去做。将这个信封里面的另外一封信亲手交给林德伯格先生,里面说得一清二楚了。不要告诉任何其他人。一旦我们发现媒体和警方都被惊动的话,那么什么安排都会立即取消,所有的事情又要进一步被耽搁了。在你从林德伯格先生那里拿到钱之后,请在《纽约美国人》上刊登如下几个字:
钱已备齐。
在得到这个通知之后,我们会给你进一步指示。不要害怕,我们不会要你那一千美元,自己留着用吧。你要做的只是绝对按照我们说的去做。每天晚上六点到十二点之间都要呆在家中,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会和你联络。
在信封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更小的信封,上面有两行字,字迹和刚才一样:
亲爱的先生:请将这封信交给林德伯格上校先生。不要通知警方,这可是为林德伯格先生着想。
尽管里面警告了不要告诉任何其他人,但是康登发觉对这样一个重大发展,自己没有办法完全一声不吭。至少,他自己说,他必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大英雄林德伯格上校。他没有汽车,因此他决定告诉他的朋友阿尔·莱克,他有车。
莱克以前是一个拳击手,案发时在房地产业工作,据称经常在一八八街和格兰特林阴大道交叉处的马克思·罗森海因酒店里出没。康登乘电车到了酒店。但是当他到达时,莱克不在那里。由于实在忍不住,康登把这封信给罗森海因看了。罗森海因建议把这封信给他们俩另一个共同的朋友米尔顿·加格丽奥看。米尔顿·加格丽奥是一个布匹商,当时碰巧在那里。加格丽奥有一辆汽车,并且同意驾车送康登到霍普维尔去。三个人讨论了他们应当如何做,最后决定,康登先打电话过去取得林德伯格家的信任,这样是最好的。
康登当时就打通了电话,但是电话被转了又转,最后转到某个自称他负责接听林德伯格上校所有电话的人那里。这个人是林德伯格上校的私人秘书罗伯特·泰耶尔。康登先自报家门,不厌其烦地详细列举了他的学历和教职。在这一点上,有不同的说法。泰耶尔说和康登通电话的就他一个人。但喜欢自我夸耀和吹嘘的康登则宣称他是和林德伯格先生亲自交谈的。我倾向于怀疑他的说法,但是无论如何,康登确实读了那封信,然后电话那边要求他打开另外一封信,并大声把它读出来:
亲爱的先生,康登先生是我们派出来的中间人。你可以将那七万美元交给他,放在下面这么大的盒子中:
康登解释说上面画了一张图,大约长、宽、高分别为七英寸、六英寸和十四英寸。然后,他继续读道:
我们已经告诉你应当用多大面额的纸币了。我们警告你不要设下任何陷阱。如果你或者其他某个人通知警方的话,那么一切都要进一步拖延了。我们收到钱之后,会告诉你到哪里去找你的儿子。你可以开着飞机来,因为那里离你家大约有一百五十英里远。但是我们会在把宝宝放到指定地点之后再等待八个小时才告诉你宝宝的具体地点。
“就这些了吗?”那边(林德伯格或泰耶尔)问道。
康登说没错,就这些,但是接着又说信件底部有两个交叉在一起的圆圈。这可引起了那边听电话的人的注意。他们商定,应当让林德伯格马上看这封信。因此,康登、罗森海因和加格丽奥就在午夜刚过之后开着加格丽奥的车出发了。他们大约在凌晨二点的时候抵达,亨利·布雷肯里奇在厨房里和他们会面。
康登被带到楼上的卧室中和林德伯格见面。一看到这封信的笔迹、错误拼写和签名圆圈,林德伯格就知道这是真的。这些都没有被公开。那个盒子的草图好像是透视图,就好像木工画的一样,这让人很容易联想起那把自制木梯。
康登对那天晚上的描述非常夸张,几乎让人恶心。他写道,当他被介绍给安妮时:
……她几乎是本能地向我伸出自己的双臂,显示出自古以来的母性本能。
“你能帮我找回我的孩子吗?”
“我会竭尽全力把他找回来。”
当我靠近一点时,我看到她那温柔的黑眼睛中闪烁着晶莹的泪水。我朝她笑了笑,摇了摇我的食指,表示对她的责备。我假装粗俗地威胁安妮·林德伯格:
“如果有任何一颗泪珠掉下来的话,我会立即撒手不管这个案件。”
她抹掉了脸上的泪珠。当她的双手离开她的脸蛋的时候,她冲我笑着,甜美而大胆。
“你看,博士,我现在不再哭了。”
“那就好,”我说道,“这可好多了。”
这个回忆录不仅几乎令人作呕,而且也和安妮对自己当时情感的更深刻、更真实的描述大相径庭。但是,这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清楚地看到约翰·康登的个性和他看待问题的视角。
罗森海因和加格丽奥开车回到了布朗克斯,但是林德伯格邀请康登在那里过夜,康登马上就应承下来。甚至还不仅如此。早上很早的时候,他就溜进了婴儿房。他到处打量,然后就伸手到他所称的“孤胆小鹰的婴儿床”上去,拿下了那两个依旧还把毛毯和床垫别在一起的别针。在玩具箱中,他取出来一些木雕的动物。然后他问林德伯格是否可以带走这些玩具和安全别针,这样如果他与绑架犯会面的话,他可以通过观察宝宝对这些动物的反应来辨认宝宝,并且可以通过问与他会面的人他们在哪里见过这些东西,以确认他们就是绑架犯无疑。林德伯格同意了。早餐过后,林德伯格、布雷肯里奇和康登到了楼上,写了一张简单的纸条:“我们于此授权约翰·F·康登博士作为我们的中间人。”这张纸条上的日期是1932年3月10日,查尔斯和安妮都在上面签了名。
媒体的问题又出来了。布雷肯里奇准备根据信上的指示在《纽约美国人》上面刊登“钱已备齐”的通知,但是如果康登在上面签名的话,记者就会立即知道他是中间人,然后会到处围追堵截他。这就意味着一切都会马上中止。
因此康登建议用他名字中的首字母JFC,后来就想出了“Jafsie(杰夫希)”这个名字。绑架犯可能能够认出来,但是其他人则不会。
在布雷肯里奇开车送他回家之前,康登花了一个多小时看小查理的照片,这样到时就可以辨认出来了。布雷肯里奇则打算住在康登在迪凯特大街二九七四号的家中,直到他们得到绑架犯的消息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