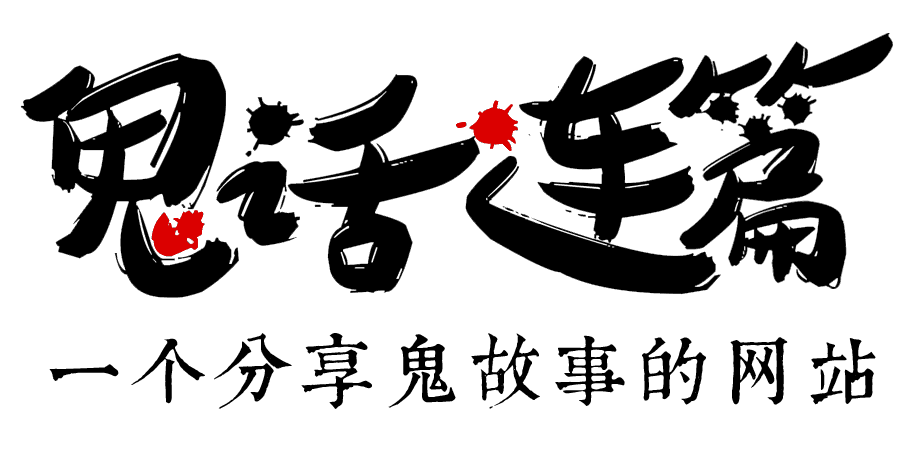因此如果你们相信丽兹·伯登是杀害她父亲和继母的凶手的话,那么在调查过程中能做些什么可能让最后的判决大体符合真实情况?根据我们在侦查支持组的许多案件中的经验来看,我认为确实可以做点什么。当然,正如在白教堂连环谋杀案中一样,这意味着假定人们有我们现在具备但当时却没有的对犯罪行为和犯罪实践的了解。但是如果当时有这些信息的话,那么我们又确实能让丽兹放弃抵抗吗?
我会试图做的第一件事是利用监狱看守所看到的丽兹和艾玛之间出现的关系紧张。利用此种紧张关系的方式之一是,和城里到处出没的无数记者中的某个记者交个朋友,准确地告诉他我们对这个案件的大体分析。我会告诉他根据我们的经验,在此种性质的案件中,几乎总有一个主犯和一个从犯,从犯自己几乎也是顺从主犯的受害者,被主犯控制,但是从犯完全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其现在一定非常担惊受怕。
我们会试图破坏主从犯之间的微妙心理关系。主犯可能想得到所有的钱,并且完全控制一切。他们之间的忠实关系是单方面的。由于这个人能够冷酷地杀死两个人,他或她也可以轻松开展下一次谋杀。而且,即使她不诉诸暴力,她也可以轻易地背叛和指责她的女恩人。
我会确保在我试图接触目标对象时,她就已经看到相关报纸文章了。这些文章可能让她心中生起的恐惧得到证实。这个策略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把艾玛和丽兹隔开来,因为丽兹的个性是如此具有支配力。
并且我不仅会将此种方法用在艾玛身上,我还会用在约翰舅舅身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是他们两个还是其中某个人知道相关内幕或者心中隐藏着对丽兹的恐惧。
当然,我还会试探丽兹。当罪犯可能面临死刑时,要罪犯直接招供是很困难的。招供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却会让他失去一切。因此我们会试图安排某种能保全面子的场景,让罪犯往里面钻。
读过《心灵追踪者》的读者还记得,拉里·金·贝尔,南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市的残忍的虐待狂,他绑架了十七岁的莎莉·菲·史密斯和九岁的德布拉·梅·黑尔米克。当时就是通过制作一份有效的行为侧写报告,外加警方一流的工作而抓获他的。警察局长吉姆·梅茨和他的探员们知道他们抓住了真凶,但是他显然不愿意招供他犯下的滔天罪行,因为这些罪行会让他坐上南加利福尼亚的电椅(最后他确实被判电刑处死)。
因此他们让我来对付他。我给他讲了联邦调查局对连环杀手的一些背景研究,我们如何管理监狱及如何了解真正的杀手心中的所知所想。
“拉里,我们的问题是,”我解释道,“当你被带上法庭的时候,你的律师可能不会让你做证,而你则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来解释你的所作所为了。这样,他们将只了解你坏的一面,罪恶透顶,一个冷血杀人犯。我们发现许多人做此类事情时,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当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已经犯下了如此罪行。”
我在这样说时,贝尔不停地点头表示同意。
我知道如果我直接要他招供,他肯定会否认的。因此我斜靠过去,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你犯的罪感到沮丧不安呢?”
这时他说道:“当我看到描述被害人家人在公墓中祷告的一张照片和一篇报刊文章时。”
“拉里,你现在坐在这里了,这是不是你做的呢?是不是?”
他看着我,眼中充满泪水,说道:“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坐在这里的拉里·金·贝尔是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是那个名叫拉里·金·贝尔的坏蛋做的。”
如果让我来对付丽兹,我会想到使用同样的战术。我首先将从现场的血迹谈起,问她到底都跑到哪里去了;她是如何洗掉的,又是如何烧掉那件衣服的。她可能比贝尔还要更复杂老练,因此我们使用的方法必须能够和她的智力水平相称,但是大约我们会这样开始:
“丽兹,根据我们的经验和研究,我们知道此种行为不像是一名妇女能够做得出来的,特别是不像一名有你这样的地位和教养的妇女做得出来的。因此如果你确实卷入其中的话,我们知道肯定有什么强大的、迫不得已的因素促使你这样做,而你对这些因素却没有明显的意识控制。我们只能想象失去亲生母亲,然后在这么多年中和雅比生活在一起,对你来说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知道她多么会操纵一切,她是如何欺骗你父亲的,她又是如何悄悄地让你的父亲背离你和艾玛的。艾玛照顾你、保护你,现在你意识到你照顾、保护她的时机终于来了,你想确保,在父亲去世之后,你和她都有很好的未来。”
我知道这番话她肯定会加以注意的。她可能会保持安静,仔细倾听,分析我说了些什么,试图想象出我到底是何方神圣,并且这对她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我所面对的是一个无辜者,那么我预计,几乎我所说的每句话都会遭到她的强烈反对。但是丽兹会慢慢上我的当的。
“你父亲那边又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他试图全力以赴地去爱你。但是请往回想想,先抛开你们之间的旧伤新恨吧。他是不是爱你爱得过分了些,或者爱的方式不对?你是如此地像你母亲,他爱你母亲可远胜过爱雅比。艾玛知道些什么吗?她看到过些什么?你可能一直把一切深埋在心中。我知道这有多么痛苦,但是我看到过其他类似的案件,我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能理解。我知道凡事总是有个理由的。他对你做了些什么?我们无法改变过去,丽兹,不论是久远的过去还是刚刚流逝的过去。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让人们理解,你为什么做了你所做的一切。我会留一沓纸给你,当想起什么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有时候这可能是最简单轻松的方式了。”
然后我就会离开,让她有时间来写写自己的故事。但是,在我离开之前,我会再说一些这样的话:“丽兹,一个做了这一切的人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帮助。她不想被关在监狱之中,而是想呆在其他某个机构之中。”
她最初可能对这一切都不屑一顾,但是,只要我能够让谈话继续下去,并让她有所参与,那么我相信一定会有些有用的信息浮出水面的。
实施此种战术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想办法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对我的采访,说我是警方从外面邀请的专家顾问。但是在采访中,我会说我和某些侦查人员及警察局的看法有些不同。我说大多数警员都认为这是一种计划周全的、冷血的谋杀行为,但是我相信这是激情式的犯罪,是出于无法控制的一时愤怒,罪犯本人在那一刻也完全不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我会说罪犯在做这些行为时就好像是在做梦一样,但是可能有什么东西让罪犯自我意识到“天哪,这可能确实是我做的”,这可以帮助罪犯为自我辩护,因此让她信任我,并且在我接下来与她交谈时,她也会乐于相信我的观点。我会让她把我看成她可能的救生索:她可能无法逃脱谋杀罪名,但我却能理解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