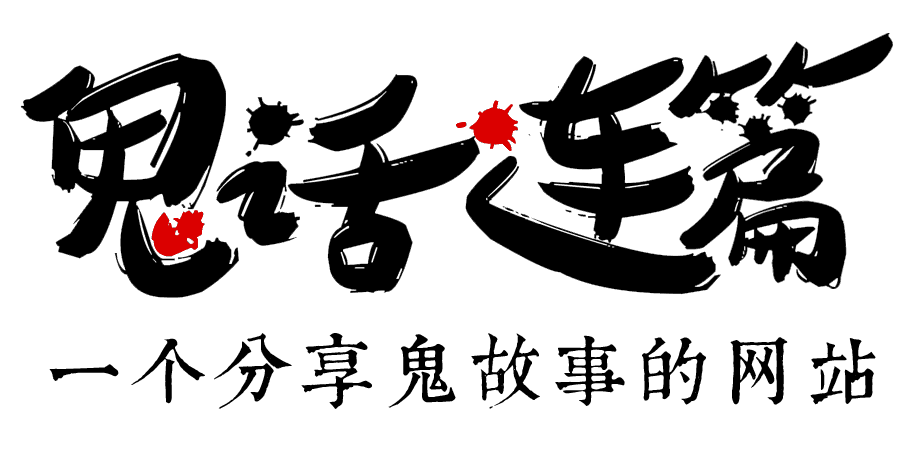艾玛和丽兹·伯登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因此她们有很多钱,用钱组织了最好的律师辩护团。除了安德鲁·詹宁斯以外,她们还聘请了四十二岁的波士顿律师梅尔文·俄亥俄·亚当斯。亚当斯曾经做过地区助理检察官,是刑事控诉方面的专家。而辩护团的核心成员是尊敬的乔治·德克斯特·罗宾逊,五十九岁,前参议院议员、众议院议员和马萨诸塞州州长。在这个被称为“缩微世界”的法院体系中——或者说在这个“利益冲突”的竞技场中,这看你怎么看了——当罗宾逊还是马萨诸塞州州长的时候,他曾经任命贾斯丁·杜威为高级法院法官,而贾斯丁现在可是丽兹谋杀案的三个主审法官之一。艾玛和丽兹支付给罗宾逊的辩护费用达到了二点五万美元之巨,这大约相当于当时法官年收入的五倍。有人称,罗宾逊开始不肯接手丽兹的案件,后来他确信丽兹无罪之后才答应下来。在第一次见面之后,罗宾逊建议丽兹开始穿黑色衣服。一旦被判有罪,他告诉丽兹,就可能被判处绞刑,尽管自从1778年起马萨诸塞州还没有哪个妇女被判处过死刑。
这是其他案件和审判中的众多手法之一,我们发现在丽兹案中这种手法奏效了。我几乎忘记告诉你们,我曾无数次将自己看到刚刚被捕的嫌疑人和数月后他在法庭上的样子作过比较。他变得干净利落,理了发,穿着比较保守的套装,眼睛看起来充满渴望、深沉而脆弱。这就等于是向陪审团说,这个极棒的年轻小伙子是不可能犯下你们刚才听到的那种可怖的罪行的。有时候,当我走入法庭,看向辩护席的时候,几乎无法区分谁是被告谁又是辩护律师。
为了帮助侯西亚·诺尔顿进行控诉,马萨诸塞州总检察长阿瑟·E·皮尔斯伯里给他派了四十岁的威廉·亨利·穆迪,他时任埃塞克斯县地区检察官,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谋杀案审判。穆迪后来成了众议院议员、海军部长、美国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在这次审判之后不久,诺尔顿就将取代皮尔斯伯里成为马萨诸塞州的总检察长。
1893年5月31日,离预定的审判日期还有五天,秋河市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件。这个事件因为发生在审判地点附近而引人注目,同时其影响也非常错综复杂。
史迪芬·曼彻斯特,乳牛场农民,送完牛奶之后回到家中,发现他二十二岁的女儿玻莎躺倒在厨房铁炉旁边,她被人砍死了。身上由于抵抗而留下的伤痕和衣服上的裂痕表明她与凶手进行了激烈的搏斗。史迪芬和玻莎两人住在农场的房子中,他此前的两任妻子都离开了,据说是因为他既低俗又刻薄。
这次还是威廉·多兰医生做的尸体解剖。他说尸体的“头盖骨及其以下部位有斧头留下的二十三处不同的伤痕”。这和雅比·伯登脑后的伤痕非常类似。
和雅比谋杀案一样,这宗谋杀也发生在早上。现场几乎没有什么血迹,没有丢什么值钱的东西。杀人犯很可能在曼彻斯特的房子内呆了相当长的时间。
对秋河市的居民来说,这宗谋杀案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被控谋杀的女犯还关在外地的唐顿监狱时,秋河市发生了一起几乎一模一样的谋杀案。这可是我听过的最好的不在犯罪现场证明。安德鲁·詹宁斯律师几乎是非常愉快地对新闻记者说道:“那么,难道警方又要说这是丽兹·伯登所为吗?”突然之间,人们就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伯登夫妇是被一个作案手法类似的无名罪犯杀害的,不大可能是丽兹·伯登。什么东西还能比这更引起人们的“合理怀疑”呢?控方清楚陪审团候选人之中的每个人心里会怎么想。
后来,在对丽兹的审判就要开始的那天,一个大约快二十岁或二十出头的名叫荷塞·克雷拉的葡萄牙移民被捕了。他曾经做过史迪芬·曼彻斯特的临时工人,和史迪芬就解雇费问题发生过激烈争执。很明显,他返回农场想和史迪芬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史迪芬当时不在,克雷拉就与玻莎交涉,并且在一时的丧心病狂之后将她杀死了。他在房子周围等了一会儿,希望等到他的主要目标回家,但是过了些时间之后,他重新考虑了一下,最后离开了。
克雷拉是一个葡萄牙人,特别是一个来自亚述尔群岛的葡萄牙人这一事实,给秋河市居民造成的影响,就像在白教堂连环谋杀案中,因发现皮革围裙而谣传凶手就是犹太人对伦敦东区人造成的影响一样巨大。贫穷、没有文化的葡萄牙移民是马萨诸塞州这个角落最低等、最遭人怨恨的种族。因此能够犯下杀死安德鲁·伯登夫妇罪行的人,很可能就是一个“葡萄牙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是不可能犯下如此罪行的。
后来证实,克雷拉直到1893年4月才从亚述尔群岛来到美国,这已经是伯登谋杀案八个月之后了。但是当这个信息公布时,伯登案件的陪审团已经选定并且被隔离了。当然,对任何其他人来说,他们心中还是照样强烈地保留着另外一种潜台词:如果一个残暴的葡萄牙移民可以闯入房内,并在一时的丧心病狂中用一把斧头或手斧杀害玻莎·曼彻斯特,而且在附近等待房主回来的话,那么,伯登夫妇遭遇的不幸可能是同样的。
对丽兹·伯登的审判于1893年7月5日上午在布里斯托尔县高级法庭进行。这可是那个世纪最为著名的刑事审判,比起德里德·斯格特案件、约翰·布朗案件、草市爆炸案,甚至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弹劾案都毫不逊色,而且它引发的兴趣和喧闹也同样如此。伯登谋杀案不仅成了秋河市居民每天谈论的主要话题,而且成了整个新英格兰的日常谈资,就像一百零二年之后的辛普森-戈德曼谋杀案不仅吸引了洛杉矶的注意力,而且吸引了整个国家人民的注意一样。正如在辛普森审判中会发生的那样,全国乃至世界的媒体都云集法庭。富裕、知名的人从没有被人砍死过,而且他们的孩子也从没有被控犯下此种罪行。如果此种事情可以发生在像安德鲁·伯登夫妇这样的人身上,那么谁都有可能身陷这样的不幸。
秋河市地区检察官诺尔顿是一个不那么积极的控诉人,是总检察长阿瑟·皮尔斯伯里硬把他拉来担任此职的。总检察长本来打算亲自参加死刑案件的审判。但是当审判日来临时,皮尔斯伯里发现,来自丽兹的支持者的压力,特别是妇女团体和宗教组织的压力,正在逐步加大。丽兹所在的“女性基督徒节欲联盟”公开宣称,联盟对她“有不会动摇的信心,她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同事和修女”。同样地,秋河市最著名教堂中心公理会教堂中丽兹的牧师们和教徒们都认为,像丽兹这样一个善良、娴静、高贵的女士是不可能犯下此种滔天罪行的。
第一天主要耗费在陪审团成员选择上了,他们都是白人男子,然后控方提出了指控。威廉·穆迪代表控方作了控诉陈词,提出三个主要论据来支持控方提出的指控:丽兹·伯登有谋杀父亲和继母的倾向,并且计划这样做;证据表明她确实这样做了,也就是将他们谋杀了;她的行为和自相矛盾的陈述表明她不是无辜的。同样重要的是,穆迪明确地指出,当布里奇特在屋外擦洗窗户、听不到屋内有什么声音时,被告人有杀害她继母的时间。接着,当安德鲁·伯登回家之后,布里奇特到自己在阁楼上的房间睡觉去了,穆迪继续说道,丽兹不在谷仓内,而是单独和她父亲在一楼。
由于没有什么搏斗的痕迹,顺理成章地,杀人犯就是某个与两个被害人都很熟悉的人,这不会引起他们的任何警觉。控方坚称,符合此种标准的唯一人选就只有丽兹·伯登了。
控方传唤了建筑师和工程师托马斯·基艾兰,政府派他对伯登住所进行了彻底的丈量。在交叉质询过程中,他承认,某人躲在前厅的衣橱中并且不被屋内任何人发现,这是完全可能的。那天下午,法官们让陪审团参观了伯登家,让他们亲自考察犯罪现场。
约翰·摩尔斯做证说,从星期三他到达伯登家里起,直到星期四谋杀案发生后他返回伯登家时止,都没有见过丽兹·伯登。最初他也被当作嫌疑人之一,但是他让警方相信他确实不在犯罪现场,并且对他在谋杀案发生期间的行踪做了详细而完全的说明,甚至连他坐过第几路有轨电车、售票员帽子上的号码和他见到的每个人的名字,他都做了详细说明。看起来就好像他事先知道需要这些证据,因此当时就详细地记下了所有一切一样。
布里奇特·苏利文做证说,她不知道丽兹曾提到的、雅比得到了一位生病的朋友送来的纸条这回事。当罗宾逊问她,当她在屋外擦窗户时,有没有可能某个人会趁她不注意溜进屋里,她承认曾在院子的某个角落里隔着篱笆和邻居麦克尔·凯利医生家的女佣聊过天。
这个案件的关键所在是作案动机问题。诺尔顿和穆迪传唤了不少证人来证明,安德鲁·伯登想立一份新遗嘱。根本就没有发现什么旧遗嘱,而且它是否真的存在也未获证明,尽管约翰·摩尔斯做证说,安德鲁·伯登曾对他说立了一份遗嘱,但是后来又做证说在他来伯登家之前,安德鲁没有提到过立了遗嘱的事。根据摩尔斯的说法,“新”遗嘱的内容是,给艾玛和丽兹每个人留二点五万美元,安德鲁五十万财产中的其余部分都留给雅比。接着,诺尔顿进一步证明安德鲁有意将他的农场留给雅比,正如他已经将当时由雅比同父异母妹妹萨拉·怀特海德居住的一所房子的所有权转到雅比名下一样。这很明显就是伯登姐妹和继母之间不和的原因。她们担心这可能明显预示着父亲对未来的安排。
当地裁缝汉娜·基福特回忆了1892年3月她与丽兹之间的一次对话。在那次谈话中,她将雅比说成是丽兹的母亲。
丽兹责备她不能说雅比是她的母亲,并且还接着说雅比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庸妇”。
“哦,丽兹,你不会真这样想吧?”基福特说她当时是这样回答的。
“我就是这样想的,”丽兹回答道,“我和她之间可没有什么关系。”
布里奇特做证说,她在伯登家的两年多时间中“没有听到这家人之间有什么矛盾,没有发生过争吵和任何诸如此类的事情”。
然而,不论如何,有关丽兹杀人倾向的证词是含混而自相矛盾的,既没能证明丽兹和她父亲之间的关系严峻而冷淡,也没能证明他们的关系正常而温暖。当然,就像当涉及人的行为时的其他情况一样,这取决于是谁在作判断。
然而,法院的两项裁决成了丽兹谋杀案最终结果的关键所在。
7月10日,星期六,控方要求引入丽兹在聆讯阶段所作的证词。乔治·罗宾逊表示反对,因为丽兹当时并没有被正式指控,并且还没有请律师辩护。星期一,法庭重开,法官不允许采纳丽兹此前做出的相反的证词。尽管在今天,辩护律师不在场这个理由对被告极为有利,但是许多法学家还是对当时这个决定感到困惑。
针对记录中出现的另外一个矛盾,辩护律师让博文医生做证,说她给丽兹注射的吗啡可能让她思维迷糊混乱。
最戏剧性的时刻还属审判的第七天。爱德华·伍德医生做证说,他检查了两个被害人胃里的内容物,没有发现什么毒药证据。他还检查了斧柄几乎完全断下来的那把手斧——警方认为这把手斧最可能是杀人凶器,但是没有发现什么血迹。他说杀人犯自己身上应当会有不少血痕。(我们还记得在谋杀案发生后的十分钟之内邱吉尔太太就看到了丽兹。)当伍德医生说他可以出示被害人的真实颅骨来说明凶器是如何被用来砍人的时候,丽兹晕倒了。好一个真正的淑女,过于敏感,无法承受如此直接的展示。法庭允许她离开。显然,陪审团成员都不会认为这一点是对她不利的。
说手斧就是杀人凶器只不过是警方的推测而已。如果警方和控方不能确实找到凶器,那么凶器可能就是被罪犯(不论罪犯为谁)拿走了,这就使得该案的关键点之一留下了让人有合理怀疑的巨大空间。
7月14日,星期三,控方传唤了药店店员艾莉·本斯。辩方提出反对。在听取了控辩双方就丽兹购买氢氰酸的企图是否和本案有关进行的辩论之后,法官们认定,本斯的证词,以及丽兹试图买毒药的全部行为,都是不相关的,因此不可采信。
然而,艾丽斯·鲁塞尔说丽兹在谋杀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曾拜访她,也就是8月3日星期三,艾丽斯讲述的情况令人毛骨悚然。艾丽斯说丽兹告诉她:“我感觉很沮丧。我感觉似乎有某个什么东西悬在我头上,我无法摆脱,并且它还无数次抓住我,不论我身在何处。”
丽兹在告诉艾丽斯她父亲和继母生病之后,继续说道:“有时候我认为我们家的牛奶可能被人下了毒。”
艾丽斯在谋杀发生当天将丽兹对她说过的话讲述给警方听,警方立即查封了伯登家的牛奶,并对之进行了测试,但是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
丽兹还提到此前有一次曾有人闯入屋内,另外闯入谷仓内的事情则发生了两次。她甚至说她曾经看到一个“奇怪的男子绕着她家跑”。
“我有时候担心父亲可能有什么敌人。”她说道。
另外一个问题是,安娜·豪兰德·伯登宣称,丽兹曾对她讲述家里的不快生活。当时她们俩(和安娜的妹妹凯莉·林德利·伯登一起)刚刚从欧洲旅行十九周回来。这次旅行是安德鲁送给丽兹三十岁生日的礼物。有人说安娜和凯莉是丽兹的堂姐妹,但是审判记录中说她们之间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当然,伯登在新英格兰地区是一个很显赫的姓氏)。安娜·伯登说,在到美丽的欧洲旅行享受了自由和兴奋之后,丽兹不想回到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中去。
当辩方律师反对引入这种说法的时候,法官们作出决定,说这一证词过于模糊含混,没有直接说明丽兹对父亲或继母有什么恶意,因此证词被排除在外。
辩方仅用了两天时间来进行辩护。他们主要是传唤了证人来证实在伯登家附近有一个神秘的年轻男子出没。他们的观点是,某个人潜入屋内犯下谋杀罪行。他们说,由于女士们都不愿意抛头露面,因此没有哪个妇女站出来说那个致命的早上曾邀请雅比,这样所谓的纸条没有办法获得证明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辩方强调丽兹身上没有血迹,并驳斥了这种说法:谋杀的方式(杀人犯和被害人的相对位置)可以让杀人犯轻松避免血迹溅到自己身上。
安德鲁·詹宁斯试图向陪审团证明如下几点:如果无法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方式证明丽兹是有罪的,那么丽兹就必须被推定为是无罪的。没有什么直接证据是不利于丽兹的,而且某些间接证据之间的链条也是脆弱牵强的。没有发现杀人凶器;没有得出什么站得住脚的动机,并且被告人的性格或此前的行为都没有表明她有能力做出如此暴力的行径;在谋杀案发生的那段时间中,其他人有机会潜入屋内。
为了抵消艾丽斯·鲁塞尔所作的丽兹曾烧毁一件衣服的证词的影响,艾玛出庭做证,说是她自己让丽兹去烧掉这件衣服的,烧掉无法洗干净的脏衣服这是家里一贯的习惯。像安德鲁·伯登这样极端节省的人的家里会有这种习惯,真是有点奇怪,况且人们都知道他家是用旧衣服来做拖把的。
艾玛做证说,丽兹深爱着父亲,并且父亲每天都戴着丽兹送给他的戒指。她强调,她和丽兹在警察搜查家里时是完全配合的,并且已经充分地证明她们没有什么好掩藏的。
对大多数旁观者来说,艾玛简直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谜。她是如此不爱交际,几乎没有人知道她有什么照片。她被说成是一个害羞、矮小、相貌平平、脸瘦、身子细的女人,总之是一个完全不出众的四十一岁的老姑娘。她在审判过程中竭力支持丽兹,尽管其中一个证人,也即中心警察局的日班女看守汉娜·里根曾做证说,在8月24日艾玛来探望她妹妹的时候,她听到这两姐妹发生了争吵。
“艾玛,你已经出卖我了,对不对?”丽兹指责道。
“没有,丽兹,我没有。”艾玛答道。
“你出卖我了,我会让你知道,我是不会、绝对不会屈服的。”
“哦,丽兹,我没有。”艾玛坚持说道。
丽兹没有为自己辩护。
7月19日,星期一,辩护律师罗宾逊作了总结陈词,强调了詹宁斯提出的各个要点,认为:如果说丽兹是真正的杀人犯的话,丽兹也不可能在不被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换下血迹斑斑的衣服,而且不可能将它们藏匿得无影无踪。
接着诺尔顿开始作总结陈词,第二天才完成。他向陪审团描述了他所认为的最可能发生的场景。他认为,丽兹杀死了她一直憎恶的继母,然后在想到她无法面对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就连父亲也一块杀死了。
在双方都完成了总结陈词之后,首席法官梅森问丽兹是否想说什么。这是她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第一次开口说话:“我是无辜的,让我的辩护人替我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