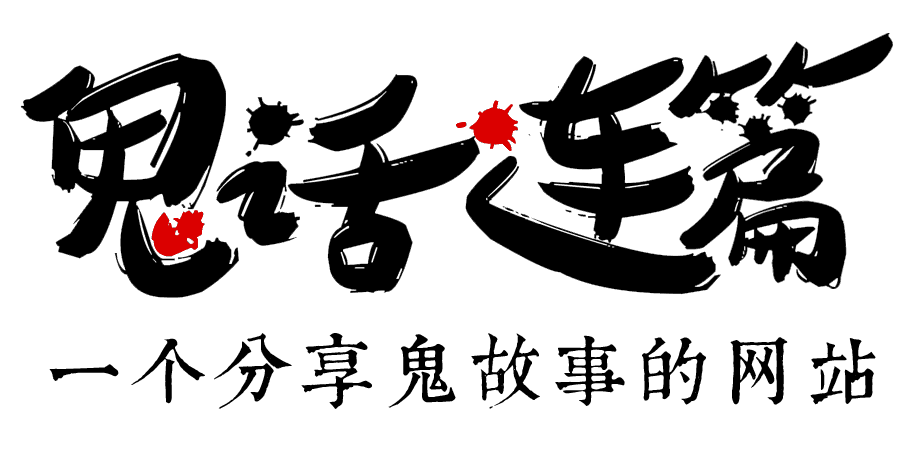第八天的夜里,奇怪的声音又响起了。
这次先醒来的是智保,随后小轮也马上醒了。这一醒,就像是从睡梦中被拖出来一样。
风铃声响了。
“丁零”“丁零零零”……又是那只铁风铃发出的声音。
“小智……”
“嘘!”智保竖起手指放在嘴唇前。
无情的声音就在近处,这种声音似乎可以击穿耳膜,令人焦躁不安,胃部也像被挤压了一下,开始疼痛。
小轮将视线上移到枕边的时钟。凌晨两点十七分。突然,风铃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传来一声沉闷的“咚”。
小轮吓得在床上缩成了一团,她花了几秒钟的时间才反应过来,那是用脚踹房门的声音。
间隔一段时间,再度响起踹门声。接二连三响起“咚”的声音。踹门声随着次数的增加变响变快。接着,门铃响了。毫无间断的门铃声、让人神经紧张的高亢噪声,一遍又一遍地循环着。
小轮心想,周边住户一定可以听得到。隔壁的住户、隔壁的隔壁住户,一定会察觉到这种异常。
救命,请大家帮忙报警。小轮蜷缩着身体,两手交握,心中默默祈祷着。
拜托了,帮我们报警吧。
恐惧。不堪忍受的恐惧。虽然小轮觉得那个柔弱的老妇人不至于把房门踹破,但是那个声音、那个踹门的声音始终不停。
太反常了。正常人绝对不会在凌晨疯狂踹别人家的房门,那是不讲理的人才会做出的事。
所以,多说无用。祈祷和哀求都没有意义。我们被抓住了。没有理由,没有逻辑,被囚禁在来历不明的事物中。
就在思考的瞬间,“嘣”的一声,小轮脑中那根紧绷的弦断了。小轮从床上“跳”起来。
“你……喂?”
话音未落,小轮已经滑下床,她身后是一脸惊愕的智保。
小轮抓起放在枕边的手机,迅速朝玄关走去。她的内心已经无法忍受,无法再等别人去报警。不能再躲在床上任凭事态发展。
她下定决心自己报警。对了,可以从猫眼处向外看,这样外面的人就可以听到自己拨打电话报警的声音了。
“你好,是警察吗?现在我家门外有一个可疑的人。请快点来,长相和服装是……”她把报警时要用到的话术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如此一来,门外的那个人绝对会害怕,肯定会在警察来之前逃走。
小轮光着脚,半蹲在门口鞋柜处。
身后的智保叫唤着什么,小轮都充耳不闻。只见她用手掌抵住房门,稍稍直起身体,从猫眼处窥视外面。
漆黑一片。怎么回事?小轮有点迷糊。
为什么?为什么什么都看不见?因为是半夜,外面才如此漆黑?不,不可能。公共走廊亮着长夜灯,而且公寓旁边也有路灯。那么,如此黑暗是……
就在这时,只见一只“眼睛”从猫眼处移开了。“哇!”小轮吓得惨叫一声,急忙从门口后退数步。对方也在向屋里窥视。
意识到这点的小轮,突然大汗淋漓,黏稠的冷汗沾满全身。不能再看了,小轮提醒自己不能再看猫眼了。
和那个家伙的距离仅仅隔了一扇门,刚刚的大叫,对方一定听到了。因此,绝对不能再往那里看了。
但是,身体却不听使唤。手脚无意识地自行移动起来,将相同的动作又重复了一遍。右手掌抵住房门,直起身体,透过猫眼窥视。
门外是那个老妇人。
黄灰色的头发,穿着那件褪色的浅棕色邋遢大衣,右脸颊贴着一大块纱布,还有脖子上的那只铁风铃。
老妇人在笑。老妇人面带嘲讽的笑容,她知道自己非常接近小轮。她很开心,欢呼雀跃着,那张爬满皱纹的脸更加扭曲。
小轮的手机从手上滑落。她的世界开始晃动,腿脚不稳,无法站立。
若非智保在身后一把抱住她,失神的小轮可能已经头朝地倒在地上了。她在智保的怀中,茫然地看着他紧绷的脸。
报警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小轮蜷缩着身体,依偎在恋人的怀中。
附近警局的警察过了四十分钟才姗姗来迟。
“我们接到了附近居民的报警。”在听过小轮一连串的讲述后,年轻警官的语气明显变得温和,“是一位老妇人吗?年龄在八十岁左右?没有,外面没人。我没看到有什么人离开。恐怕是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不知道去哪儿才在这里徘徊的吧。”
“不,没有感觉到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对话的时候也是应答自如。”小轮继续说明。
“啊,这样啊。看来你们认识啊,都能在一起说话。”警察自顾自地下了结论。
小轮急忙打断他:“等一下,您搞错了。我压根儿不认识那个老妇人。深更半夜的,她这么三番五次……不管怎么想都会觉得这事儿很奇怪吧?拜托您认真地听我讲。”
警察摇摇手:“好吧,就当她没有得阿尔茨海默病,其实各地的老人都会干出这种事。他们很孤独的。”
“孤独?”
“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啊。我也知道他们很烦人,但也请不要对他们太凶。”
小轮看着面带苦笑说出这番话的警察,哑口无言。
双方的对话仿佛不在同一频道上。连日来经历了怎样的恐怖、对那个风铃声是何等恐惧,根本无法让眼前的警察感同身受。
就因为对方是“老人”。
“不是像你说的那样,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
“好了,好了,请你冷静下来。”警察用手势示意小轮闭嘴。
“那个老妇人啊,一定觉得你长得很像她的孙女,所以才会以这样的理由三番五次来你家门口。反正也没有对你造成实际的伤害,对吧?不过就是一个老妇人,别那么紧张,放松心情。”
“别那么紧张?”小轮再一次哑口无言。她在背后暗暗握紧拳头,让自己冷静下来,再开口问道。
“也就是说,您不会帮助我,是吗?”
“我们警察也不是什么事都能解决的。没发生事情,我们也不能行动。要是发现了那位老妇人,我会提醒她别去了,让她引起重视。这样行吗?”
显然,警察并不重视小轮的诉求。
他的态度也好、用词也罢,无不透露出不耐烦的情绪。“别为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妇人大惊小怪,这种事情你自己可以想办法解决。”虽然警察嘴上没明说,但他的眼神已经告诉了小轮。
“对不起。”警察离开之后,智保嘟囔了一句。
“什么意思?”小轮回头看着他,“为什么道歉?”
智保没有回答。小轮继续说着,情绪也越发激动。
“你为什么要为今晚的骚乱道歉?理由是什么?你告诉我,你刚才说的‘对不起’到底是在对不起什么!”
沉默笼罩了整个房间,一片令人喘不过气的沉寂。片刻之后,“对不起,把你卷进来了。”智保轻声叹道。
“到底怎么回事?”小轮追问道。
“不,不,我……我不想这样,已经半年多没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以为大概结束了。所以……是我大意了。我不想让你感到困扰,希望你就知道这些。真的非常对不起。”
半年多,没发生什么事情,以为大概结束了,大意了。小轮在消化这些语句。
也就是说,这事情并非是近期才开始的,而是长时间追随着他。为什么?何时开始的?究竟持续多长时间了?
“……你……来到这个城镇前,住在哪里?”小轮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小轮知道智保是个聪明人,做事认真、勤奋,没有一点轻浮,和那些素来居无定所、到处流浪的人明显不同。
“你之前在哪里生活?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的家乡在什么县市?在什么样的地方长大?你的名字是真的吗?喜欢看电影的外公是真实存在的吗?到今天为止你跟我讲的话,有多少是真的?我……我对你一无所知!”
小轮接二连三抛出疑问,如决堤洪水。
直到现在,她都在努力控制自己去追问,她多么想等智保亲口告诉他。所以,当事态变得不可控制时,小轮忍耐的极限也到了,就像泄洪的水,冲口而出。
智保依然沉默,纹丝不动地戳在小轮面前。只有耷拉着的眼皮在微微抽动,紧闭的双唇和握紧的双拳,如同石头般无法撬动。
小轮越来越焦躁,一拳打在智保的胸口。但是,智保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一拳,又一拳,再一拳……终于,智保的双唇哆嗦着微张开:“对不起。”
小轮放下了拳头。她明白了无论跟他怎么说、怎么打他都是徒劳的。因为智保毫无反应,犹如拳打棉花一样有劲使不上。
智保别过脸去,不再看小轮的脸。他紧紧地闭上眼睛。
小轮半张着嘴,还没想好接着要说什么。不管怎样,主要是想跟他倾诉,想呼喊他的名字。
但是,风铃的声音撕裂了空气。
“丁零”“丁零零零零”……
“听,听见了吗?”
小轮抬头看着智保,对他的恼怒瞬时抛到了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翻腾而来的恐惧。
风铃声在某处响起。不是来自附近的声音。但是,它乘着风,清晰地响了起来。
“丁零”“丁零”“丁零零零零零”……
“这……我幻听了?还是,那声音真实存在?”小轮用双手捂住耳朵,她感到自己的手掌心已经沾满了潮湿的汗水。
“我好像要疯了。”这不是夸张。
小轮确信,如果此刻房门再被踹上一脚,她一定会疯。紧绷的弦会随着张力彻底断开。恐惧、害怕的感觉浸润全身。
不知道过了多久,时钟表盘上的指针指向了六点,外面逐渐明亮起来。亮光透过紧闭的窗帘射入房内,天空的边缘正在变白。这个漫长的黑夜,终于结束了。
随着早晨的到来,夜晚还会如约而至。太令人胆寒了,无法形容地害怕。小轮一直用手捂着耳朵,蹲在地上。
那天早晨。智保丢下一句“我出门了”,便离开了公寓。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夜里,时钟走过了七点,又走过了十点,他还是没有回来。
小轮没有办法,只能一个人度过夜晚。她紧闭窗户,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门锁及U形锁反反复复确认无数次之后,才爬上床去,并且她在枕边放了一把水果刀,至少可以当成防身的武器。
不过,夜里并没有响起风铃声。
第二天,小轮给“小田环境开发”打去了电话。
“您找岸是吧,他昨天辞职了。”一位认识智保的职员礼节性地回答道,“打零工的职员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辞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第三天、第四天,智保依然未归。
与此同时,风铃声也再未响起。
智保原先放在地板固定位置的电影剪贴本和那个皱巴巴的双肩包都不见了。不过,小轮买来给智保用的马克杯和筷子还摆在原位,算是他曾经在这个房间里待过的证明。
小轮终于想明白了,智保从最初就没想过要在这里久居。他子然一身,不会增加额外的行李,方便随时离开,甚至连一只袜子都没留下。
在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她开始准备放弃这段感情。
记忆是很难磨灭的,她在茫茫人海中看到身高接近智保的男性时,就会下意识去追寻。走路的时候,她会有意无意地在人群中不断找寻他的身影。
然而,时间慢慢平息了她的爱意。当小轮对公司同事坦荡地把这段奇妙的失恋经历说出来的时候,日子又过了一个月。
当然,智保是“小田环境开发”的工作人员这点不可能明说。
“虽说是走得很近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跟踪。同居的人什么都没有解释,就这样消失了。”小轮说得有点模棱两可。
“要我说啊,这不就是跟踪案件。”在听完小轮的话之后,女同事自信满满地断言,似乎把智保当成了女性。
“逃避家暴丈夫的人好像都有这种感觉。这种人跟谁都可以平淡地交流,但不会对任何人敞开心扉;总是做好逃跑的准备,不会额外增加行李,仅随身携带重要物品;不会对别人说出某些事情的深层原因以及个人情况,还有点神经质,总是在害怕什么,然后突然有一天,毫无征兆地人间蒸发。怎么样,我说的都对得上号吧!”
原来如此,小轮心想。
她从没想过给那个老妇人扣上“跟踪狂”的帽子。听同事这么一说,二者倒是吻合。
一听到跟踪狂这个词,脑海中就会想到“痴情种”“前对象”。结合智保的态度,他确实很像被跟踪狂跟踪的人,毕竟他长着一双容易让人意乱神迷的眼睛。
莫非智保?不,不可能,小轮无法想象他和那个“老妇人”有男女关系。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智保确实有在被追求的可能。不管年龄多大,女人毕竟是女人,况且智保称得上是有魅力的男人。
智保现在在做些什么呢?
估计他又在某个城镇里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随后那个“老妇人”会再次找到他吧?
尖锐的风铃声,在脑海深处苏醒。
小轮深深地叹了口气。
又过了一段时间,就在内心伤痛即将痊愈时,小轮在影碟租赁店里发现了《恐怖角》。经过一番犹豫,小轮拿着影碟走到柜台前。
回到家后,小轮立刻打开播放机。果然是一部讲述跟踪狂的电影。
不过,这部电影演的不是男女之间由爱生恨的故事。影片讲述了一个强奸犯认为自己入狱是因为他的辩护律师对自己做出了不利的指证,于是怀恨在心,追着律师一家一步一步地展开隐蔽的骚扰。
在电影的前半段里,强奸犯对律师进行跟踪、监视,杀死律师家的宠物狗……这种精神暴力令人备受折磨,犹如用棉线勒住了脖子。
电影结束后,小轮将碟片从播放机里取出,拿起手机,打开谷歌搜索页,在搜索栏内输入关键词“跟踪狂”。
网页上跳出“被跟踪者逃跑”“非情感纠纷的跟踪管控法”“警察救助被跟踪者”……
小轮一个劲儿地滑动着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