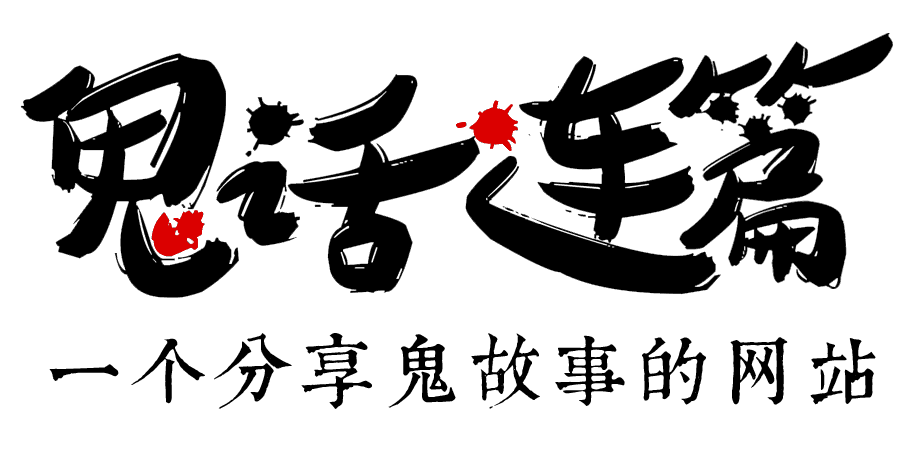一天,某人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
那是距离春天来临还很远的冬天。小轮嘴里一边轻声念叨“真是个讨厌的天气”,一边加快步伐朝公寓走去。她相信了天气预报的预测,没带伞。当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被有史以来最温暖的冬天和连续阳光灿烂的日子弄了个措手不及。
可是今天的冷风“飕飕”地刮在她的脸颊上,和昨天相比完全是两个季节。穿过肺部的空气都是干燥和沉重的。飘落的不仅是雨,还夹杂着雪。
小轮急匆匆地想赶在雨势变大前回家,但她今天穿着一双浅口单鞋,不太能跑,这让她感到沮丧。
好不容易回到公寓,小轮终于松了口气。
一般来说,小轮比智保要早到家三十分钟。她走上公寓的外墙楼梯。每登一步,浅口单鞋的后跟就和金属的阶梯碰撞,发出嘈杂的声音。
小轮心想:“今天晚饭吃火锅吧。”
就在这时,她发现有一个黑影正蹲在公共走廊里。黑影在二楼最里侧,正对着小轮和智保居住的房间——一个人靠着围栏坐着。
小轮看着那个身影,陷入沉思。
小智?应该不是。
她有那么一瞬间怀疑是小智忘带钥匙才坐在门前等她,但不是。那个影子比较小,比智保的要小两圈。
小轮提高了警惕,向那个身影走近。随着越走越近,那个身影也变得鲜明起来。
是个“老妇人”。
她坐在水泥地上,一条腿放平伸直,另一条腿则弯曲着,双手抱住弯曲的膝盖。一绺黄灰色的头发从包裹着头的围巾里掉出来。一绺流苏在冷冽的寒风中飘荡。身上穿着一件大衣,原本应该是浅棕色的,眼下已经褪色发暗,貌似穿了很长一段时间。
小轮猜不出“老妇人”的年龄。在她的印象里,老人的脸都大同小异。但眼前这个人的脸——被太阳晒得布满皱纹,看起来应该有八十岁。
“您,那个……”小轮战战兢兢地说道。
眼前的老妇人肯定不是这个公寓里的住户。应该是迷路了,或是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她是在公共走廊的屋檐下躲雨吧。小轮寻思着是否应该在下雪前报警,让老妇人得到保护。
“啊,对不起。”老妇人说着,将伸直的一条腿缩了回去。
这是让小轮出乎意料的声音和动作。小轮松了口气,即使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也不像是重症。
“来,请。不用管我,请进。”老妇人笑着催促着小轮。她的声音听起来带着一股被酒精灼伤般的嘶哑。
“好,好的……”小轮感到既吃惊又害怕,她避开老妇人,站在了自家门前。
“那,那个,您是找人吗?还是,您迷路了?要不,我帮您叫巡警来吧。”
“啊,没事,没事的。你请,别管我。”老妇人摇了摇手说。
她的右脸颊上贴着一大块纱布,脖子上不明所以地挂着一只铁风铃,从她那件暗淡的浅棕色大衣胸前露出来,随着老妇人的动作发出“丁零丁零”的声响。
“我只是累了,想在这里坐一会儿而已。别管我,请,你请。”
“嗯。”小轮无能为力,背对老妇人,将钥匙插进门锁,迅速闪进室内,然后将房门反锁。她又从猫眼里向外张望了一下,老妇人保持着跟刚才一样的坐姿。
小轮还在纠结,不报警真的没关系吗。但是,通过简单的交流感觉老妇人很稳健,也不像腿脚不利索的样子。小轮又想了一会儿,才突然意识到既然她走累了,为什么还特意登上楼梯,走到二楼走廊的最里端?一楼也有公共走廊。正常情况下,老人感到腿脚累了,会选择在一楼的檐端休息。那她究竟为什么要特意爬上楼梯,甚至走到最里侧的房门前坐下呢?
莫名其妙。正因为不明所以,小轮突然觉得那个老妇人让人瘳得慌。
小轮迅速将U形锁扣了起来。平时,智保回来之前U形锁是不会扣上的,但那天,仅是锁上门锁依然让小轮感到不安。
小轮心中不停地祈祷,希望智保能早点回来。她匆匆忙忙将浅口单鞋脱了下来。
“小智,那个老妇人还在门口吗?”小轮开口问已经回到家的智保。
“老妇人?”智保有点不解。
看到智保的反应,那位老妇人应该已经不在门口了,小轮终于如释重负。
“实际上,今天碰到了一件可怕的事。”小轮向智保倾诉,“有个不认识的老妇人,正对着我们家门口坐着。她嘴里说‘累了,坐一会儿’,既然累了还爬上二楼,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一开始以为她是老年痴呆,但跟她简单交流后又觉得不像。不知道她要干什么,总觉得心里毛毛的。”
心情舒缓了的小轮滔滔不绝地说起来,甚至没有注意到智保并没有接她的话茬儿。
“虽说对方是老妇人,但我一个人待在房间里还是有点怕。说真的,我已经好几次想要报警……”
突然,她的双肩被智保紧紧抓住。“……‘她’长什么样?”
“啊?”
“脸长什么样?什么打扮?”
智保的神色变得异常慌张,小轮不知所措,直眨巴眼。感觉到他抓住双肩的十指传来的力道已经透过衣料,深深地嵌入皮肤中。
“长什么样?没,没什么特别,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妇人。但是着装有点奇怪。她的右脸颊贴着一大块纱布,脖子上挂着一只铁风铃。”
一眨眼的工夫,在小轮近距离的凝视下,智保的神情凝固了——他的脸颊失去了血色,变得惨白。
“智,小智?”慌了手脚的小轮,呼唤着恋人的名字。肩膀依然被他紧紧抓着,她对着眼前这个目光呆滞、怅然若失、精神恍惚的男人又呼喊了几次。“小智,喂,你到底怎么了?”
足足数十秒后,智保才缓过神来,双手同时放开了小轮的肩膀。
“……对不起。”说着,智保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对不起,我今天身体好像有点不舒服。头好痛……可能感冒了。不吃晚饭了,我去睡了。”
从那天起,智保完全变了一个人。
他每隔两个小时都会给小轮所在的公司打电话,问她:“没事吧?”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还时常在半夜里被噩梦惊醒,对周遭的声响也变得极其敏感。
在观看租来的影碟时,智保不仅会哭出声来,甚至抽抽嗒嗒哭个不停。那是一部关于少年棒球的电影。描述的是一支弱小的队伍变为强队,并在联赛中过关斩将,拼到最后夺冠的故事。教练会在重要比赛的关键时刻,换下主力队员,让技艺不高的板凳球员出场,感受比赛的气氛。
这个桥段看得智保那豆大的泪珠不住地流,激烈的呜咽声,几乎让小轮因为感动而落下的眼泪憋了回去。
“我,我也……”智保哽咽着说,“我也打过棒球……在我还小的时候。后来中途必须要转校,从此以后就再没碰过棒球。我也没有想过继续在其他队伍打球。虽然我的妈妈鼓励我继续打下去,但是……”
说到这里,智保就再没说下去,然后就只有他啜泣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
小轮闭口无言。
在一起的这些日子里,智保对于过去只字未提。他出生在哪里?父母双亲、兄弟姐妹还健在吗?小时候就读于什么学校?在学校做过什么?小轮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她觉得不知道也无妨。
“听好了,你真有了想亲近的对象,千万不能刨根问底。”这是小轮的母亲时常挂在嘴边的话,“刨根问底地问别人是非常失礼的,千万别这么做。你能做的只有等待。如果对方把你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终有一天,对方会开诚布公地对你袒露一切。”
其实小轮早就隐约感到,智保一直在回避关于双亲的话题。从他嘴里听来的全是他外公的事情,而且全是外公和电影相关的事情。像刚才那样,从智保嘴里谈及过去发生的事情时,说出“妈妈”这样的称呼还是头一遭。
“……没事了。”小轮向着还在哭泣的智保轻声私语。“没事了。现在我在你身边,一定没事的。”小轮觉得这句话很空洞,但也只能这么说。
她伸手触摸了他的肩膀,又在背后抱了抱他,其实小轮内心还想去抚摸一下他的头发,不知为何又做不到。
关了灯的房间里,充满了智保低沉的啜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