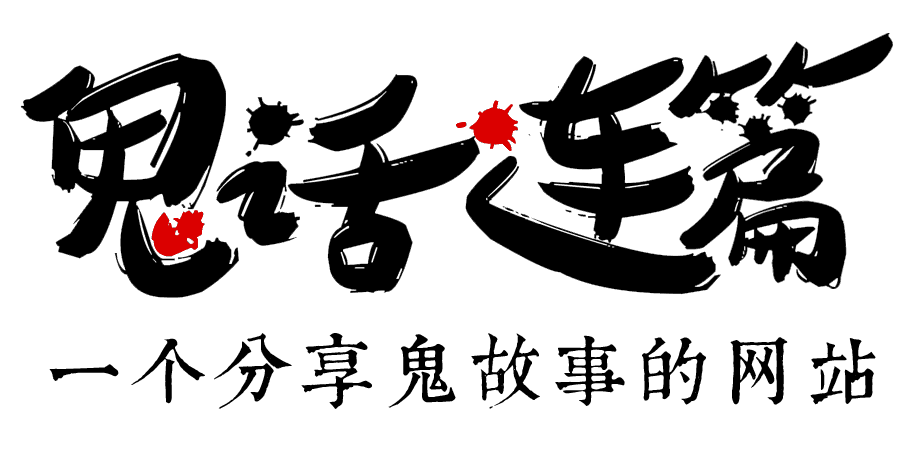2000年8月19日,星期六,11点26分
莫尔塞岛,海鸥湾谷仓
在瓦雷利诺手枪的威胁下,阿尔芒、马迪和我都进了谷仓。
再一次,谷仓里发霉的食物味道让我喉咙反酸。马迪和阿尔芒进来后也在观察角落里堆着的箱子,打翻的椅子,以及墙上乱爬的虫子。
我没办法说出一个字。我试图吸引父亲的视线,向他表达我的不舒服和不理解。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一个眼神就能让我放下心来。没事的,这是个计谋,我晚点儿给你解释。
但是没有,父亲一直躲避我的眼神。他完全没把我放在心上,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瓦雷利诺和父亲让我们坐在谷仓最里面脏脏的箱子上,他们两个在大声商量。
“我们要怎么处理他们?”瓦雷利诺问道,“如果开枪的话,动静太大。现在岛上气氛比较紧张……得赶紧做决定!”
父亲还在思考。这一次,轮到我在躲避马迪和阿尔芒的眼神了。他们似乎在问:你父亲在干吗?
我没有答案。肯定是有原因的。
“你说得对,我们没的选。”父亲回复。
他紧张地把桌子上的物品全部清空。水果烂掉了,葡萄和苹果掉在地上变成一团稀泥。他双手撑在桌子上,然后转头看着我。
“科林,我最后问你一次,你什么都不记得吗?在那顿饭之前或者之后,或者吃饭的时候,关于疯狂马萨林的任何线索?”
我说不出话。
“爸爸。”
这既是疑问也是请求。
10年来的希望都包含在这一个词里。
父亲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同伙。
“文件里有张地图,我看过,但还不够。”
“算了,管他的。”瓦雷利诺回答。
父亲还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你说得对,没有他我们也能搞定。”
“没有他”这几个字像一把尖刀穿透了我的心。为什么他不敢当着我的面说这句话:“没有他我们也能搞定。”
我感觉身旁的马迪在缓缓移动。她看到右前方2米的箱子上有一把餐刀,一把生锈的刀。我没有勇气去劝阻她。
“我们还差最关键的!”瓦雷利诺吼道。
父亲拿起我从公证员那里拿来的米色文件夹。
“这里有证据,这是最关键的,不是吗?我们一起看地图,会找到的!无论如何,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这个“他”再次穿透了我的心。
“你只会这样说。”瓦雷利诺很生气,“为什么没法让他开口呢?”
“我正在做这事啊,结果你的枪被人偷了!”
“是是,好吧,我们赶紧了结此事,不能再待在这里了。”
马迪一瞬间从箱子上跳起来想抓住小刀。她刚刚把手放在刀把上,父亲的大手就扣住了她的手腕。
“松手,不然我会弄疼你的。”
马迪没有退让,她试着扭动手臂,应该是来自她学过的巴西柔术的灵感。但是父亲紧紧抓住了她的另一只手臂,然后扭转到后背,马迪疼得大叫,最终放弃了武器。
父亲把马迪推到我们这边。
“浑蛋。”马迪跳着说,在面前吐了口痰。
我的脑子要炸掉了,没法思考。刚刚发生的事情在我脑子里回荡,我无法理解。
然而最坏的还在后面。
父亲从地上拿起几个旧箱子,掀起一块油布,下方应该是谷仓的酒窖。他打开了酒窖的木门。
“你们三个进去。”
我们还没来得及反应,瓦雷利诺把枪指向我们。一个词,两个音节,在我脑子里回荡。但是我没法说出口来。
爸爸。
如果我能说出口,如果我能捕捉他的目光,他就没法忽视我。还是有希望的。要有信念、爱和敬意。
阿尔芒和马迪已经走进了那个酒窖。
我是最后一个。
我张开嘴,但是父亲转过了身。
他走了几步路,俯身从角落里的箱子里拿出一把长长的电缆。
他无动于衷。
我什么话都没说。
我安静地走下了最后几级台阶,下面是黑漆漆的酒窖。瓦雷利诺弯下腰来看我们,我居然庆幸我看到的最后一个画面不是背过脸不看我们的父亲。
“没多少人知道这个酒窖的存在。”瓦雷利诺说,“你们也别心存幻想。你们只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来到了一个错误的地点。”
他盖上油布,整个酒窖陷入一片黑暗中。我们不说话,连呼吸都不敢出声,听着上面的动静。我们等着关门的声音,或者是家具移动的声音,但什么都没有。
死一般的寂静。
持续了一分钟。
突然一阵剧烈的嘈杂声。
不是家具倒在油布上面的声音,而是上方整个建筑物坍塌的声音。
“我们得逃出去!”阿尔芒尖叫,“整个谷仓都塌了,我们被困在地下。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没有人知道这个酒窖的存在。就算有人经过,就算我们疯狂大叫,也没人听得到。”
马迪不开口。
在黑暗中,我看不见她。她还在吗?
“我们死定了。”阿尔芒很恐慌,“我们会饿死在这里的。”
在黑暗中,不知道身处何处的马迪说出了最可怕的一句话,我甚至无法责怪她:“科林,你的父亲挺酷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