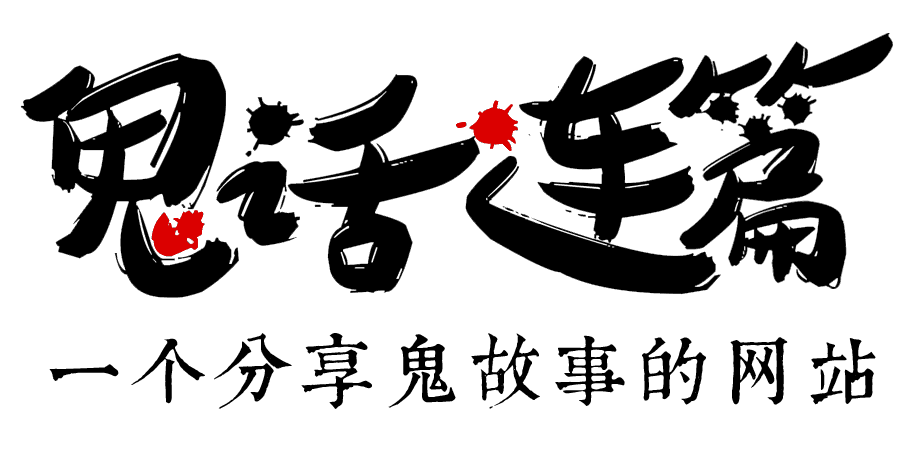2000年8月18日,星期五,1点17分
莫尔塞岛,半岛营地
大家都在大帐篷里睡觉。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微光,辨别出6个躺着的人。我晚上睡得不多,一直在想白天发生的事情。
一方面,见过了保姆、记者,跟奶奶打了电话,他们都确认我父亲已经死了!
但是另一方面,他溺水10天后被发现的尸体,蒂埃里和布丽吉特的沉默,还有前天与父亲的偶遇,都说明父亲的死亡不是事实。我父亲是个英雄,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一个好人,一个杰出的人物。一个厉害到可以编造自己死亡消息的人。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销声匿迹。
这样就解释清楚了。他不相信任何人,如同记者所说,甚至连他的小舅子都信不过!他当时被人威胁,直至现在还没摆脱威胁。他的坟墓刚刚被人泼过漆,这就是证据。
我父亲还活着,但是身处危难中。他装死是因为他被人威胁。这样就说得通了。
我回到自己的睡袋里。有一个男孩子约翰咳得比较厉害。
我之前跟马迪还有阿尔芒讨论了很久。他们听得很认真,尤其是马迪。我试图将前后矛盾的地方说圆了。我是唯一可以帮助父亲的人。他需要我,尤其是现在。
我又想到了墓地里的流浪汉。我确定他跟监狱的逃犯没关系。他比他们年龄更大,而且他也没想藏起来。现在整个法国西部的警方都在追捕一个逃犯,如果他是逃犯肯定会躲起来。他的话在我脑海里回荡:“我知道你父亲在哪儿。”
我真是蠢货!
我居然被吓跑了。这个男人是我唯一的线索。一个能帮我找到父亲的人。我得再找到他。
在这样一个旅游小岛上,应该没有很多他这样的流浪汉。《小岛人》的记者肯定认识他。
我在脑海里盘算着明天的行程。下午划帆船,根本没时间啊!或者是装病……但是这样的话,杜瓦尔神父就会跟着我。不,这样反而会吸引注意力。这是自杀行为。我还有一整个上午。将近11点,大家都会去海滩。11点之前,还比较平静。起床、吃早餐、上厕所、洗碗、闲逛。如果有马迪和阿尔芒帮我掩护,运气好的话,其他人不会注意到我不在营地。
如果我早点儿起床,就可以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我得动作快点儿!蒂埃里和布丽吉特明天到,到时候我就没法单独行动。
他们从头到尾都在撒谎。
我只有一个早上的时间寻找我的父亲!
明天太迟了!
明天……我想了想,明天是星期六,8月19日,我16岁的生日!
我的生日……这一系列巧合在我看来太奇怪了:父亲的出现、杀手的到来、被亵渎的墓碑、那个跟我搭讪的流浪汉、我的生日……这几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一场预先排练好的交响乐,然而我不知道谁是幕后的指挥者。
凌晨2点,我还在跟困意作斗争。
我又想起了修道院废墟里吃晚餐的照片,还有那段视频。
最终困意占据了上风。
我揉了揉眼睛。
灰尘很刺眼。我看到上方是一群大人,他们个子高大,围坐在桌子旁。我看不见他们的脸,只看到一条条腿。光溜溜的大腿,裙子,短裤。父亲的手伸过来,我认出了他无名指的戒指,一个很简单的银质婚戒。母亲戴着同款。这是她留在我记忆中最后的几个画面之一。她最后一次来到我床边跟我讲话时也戴着这个戒指,之后她就在车里自杀了。父亲的手揉着我的头发。我呵呵笑,真是太舒服了。
突然画面转成了噩梦。尖叫声代替了笑容。
我不明白,捂住了耳朵。父亲的手牵着我的小手,让我很安心,好像是在对我说没关系。大人们在争吵。然后父亲的手松开了。我不想他离开,大声尖叫。我感觉快要陷入地下。
桌子离我越来越远,尖叫声越来越大。我只牵着父亲的一个手指头。他松开了,远离我。最后的画面是父亲的手放在他的啤酒肚上。我一身汗醒来。才刚刚凌晨3点。
早上,我等悠悠过来,他每天8点半来到帐篷下签到。我在睡袋里已经穿好衣服,提前半个小时准备好一切。等悠悠一离开帐篷,我就跳出睡袋。马迪和阿尔芒知道接下来怎么做,我们一起拟订了作战计划,例如:科林在厕所里。科林跟马迪在一起。科林跟阿尔芒在一起。我们刚刚见到了他,他在那边……这两个小伙伴值得信赖。
我从帐篷出来时很小心不要遇见任何人。我随时有可能遇上斯蒂芬妮、杜瓦尔神父或者是悠悠。幸好农场的院子里树木繁盛,我在树荫下穿行,就这样毫无困难地离开了营地。早上清新的空气让人感觉良好。一阵轻柔的海风刮在我脸上。我几乎两个晚上没睡觉。沿着修道院大街走着,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早在小岛上散步。红宝石湾升起的朝霞微微泛红。也许这个名字就是由此得来。
我现在彻底醒了,感觉内心充满了力量。明天我就16岁了!又大了1岁。我感觉一天内长大了10岁。红宝石湾似乎恢复了平静。沙滩入口处还拉着警戒线,但是没有游客,没有看热闹的人,也没有囚车。小岛出奇地安静,大马路上也空无一人。潮水退去。就连钓鱼的人也不见踪迹,只有被人遗忘的水坑。
暴风雨后一片安静,仿佛整个小岛被清空了。我昨晚读了《小岛人》报,仔细观察了上面逃犯的模样,还有文章里提到的其他细节。
两发子弹,一发在背上,一发在脖子后。
万一营地有人发现我不见了,我得找个说法。杜瓦尔神父本来一筹莫展:营地周围有在逃囚犯啊!他昨天花了半个多小时训诫我们:不能走远,不能单独行动,时刻保持警惕。然而今天早上一切看起来很平静。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骑单车的还有跑步的……不过他们都是成群结队的。
到达圣—阿让港口时已经9点了。有几个常客在大科莫兰酒店的露台喝咖啡。看不到记者的踪影。我叫来了服务生,问他是否见过《小岛人》的主编。他笑着说德尔佩什11点才会出现,他一般前一晚都在忙着报纸的发行……
于是,他给我指了报社的位置,位于跟港口平行的大街——奥里尼大街上,离这里几米远。
我赶紧冲过去。穿过1908-5-20广场时,我看了一眼马萨林雕像。然后又扫射了一眼四周,担心那个流浪汉会出现在街角。
没有人。
奥里尼大街上《小岛人》的牌子很醒目。它由贝壳拼贴而成,十几个重复的画面叠加在一起,最后组成一个巨大的问号。真是有够疯狂的。今天的头条已经贴在了橱窗上。大标题是:让—路易·瓦雷利诺被过去抓住了。
这个记者说的过去是什么?我记得他昨天在港口说的那些话。文章开头确定了我的想法:记者提到了嗜血者工地的事故,瓦雷利诺可能参与其中,他当时在市政府工作。这个事故牵涉到很多人……我的父亲没有出现在文章里。这让我很好奇,但我得耐住性子,把问题一个个解决掉。首先,我得找到墓地那个流浪汉的踪迹。《小岛人》的总部关门了,上面的海报写着:下午2点开门!
错过了!
现在将近9点30分,我赶回营地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我手头没有线索。谁可以告诉我一个流浪汉的消息呢?去街上问商人吗?为什么不可以?我想了想,右手边是商业街,后面是大海和港口。前方是5-20广场,一直往前就是市政府。
为什么不去市政府呢?
我来到市政府的院子里,看到一辆红色的山地车朝我这个方向骑过来。
我马上认出了他。他就是所谓的“安全负责人”,总是骑着单车在小岛上转来转去。人们经常在沙滩、自行车道上看见他。他看起来总是一脸严肃,询问悠悠一切是否都好,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他。
这个骑单车的家伙可烦死人了!
然而如果说这个小岛上还有谁知道流浪汉的踪迹,那就非他莫属了。这就是他的工作啊!公路安全负责人。他把单车停在台阶上,一副牛仔的潇洒范儿。
“先生?”我问道。
他转过身。
“嗯?”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他装出一副很忙的模样。但我还是继续问:“我在找人。一个老流浪汉,穿得破破烂烂,灰色长头发,几乎没有牙齿了。你应该见过,这个小岛上这样的人不多。他看起来有点儿吓人。”
这个公路安全负责人笑了。
“小家伙,这个小岛上让人害怕的人可多了。”
这个家伙太过分了,居然叫我“小家伙”。他也不过比我大10岁而已。但我还是扮演乖学生的样子。
“好的,先生。”
“你欠这个食人魔什么东西吗?”
笨蛋!我没有预见他这一招。
为了争取时间,我转过身,看着市政府建筑的正面。我第一次注意到上面只有“自由”二字,其他的字不见了……
很奇怪。
这个家伙注意到了我的视线,我又赢得了几秒钟来想对策。
“这个,我正在小岛度假。我参加了杜瓦尔神父的夏令营,就在半岛那边。我想那个家伙也许是我的亲人,可能是我表哥……我好像认识他。我想找到他。”
他看着我,一脸奇怪的表情。
“你的表哥?”
他又看看手表,一副很着急的样子。
“你要找的人不是流浪汉,只不过是个穷人,喝多了而已。他以前是水手。他不是坏人,但是商人们不喜欢他在村子里闲逛,会影响到游客。其他没什么问题。他不乞讨,就是个酒鬼而已。”
“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真的是你表哥?”
他看起来很怀疑我的说法。
“是的,我很确定。我父母明天过来给我过生日,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他。”
我这一次看起来很真诚。
“夏天的话,他一般住在海鸥湾上面的谷仓里。你肯定能找到那个地方,是个破房子,屋顶是铁皮的。海边只有一家这样的房子。他从早上睡到中午,下午也在睡觉。”
他又看了一眼手表。
“好了,我得走了,小岛上情况紧急。别一个人到处逛,小家伙。现在可不行。”
他给我使了一个眼色,然后走进了市政府。
浑蛋!我讨厌大人这种眼色。但无论如何,我拿到了我想要的信息。
太棒了!
9点37分。
我算了一下时间。我正好在小岛的另一边,离谷仓差不多4公里。我看到了公路安全员的单车。电影里不是经常有偷单车的桥段吗?但这个想法也只是一闪而过,我不想被作为罪犯带回营地。
4公里?不怕,冲啊!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跑。天气不是很热。要知道以前我从没跑过2公里以上!
跑了500米后,我感觉膝盖快不行了。我大汗淋漓,心跳加速。
我停下来,改成大步走。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9点41分。
再次出发,这次好多了。我又跑了1公里,再次停下来,改成大步走。小路蜿蜒向上,但我没有停下脚步。来到平路时,我继续冲刺。
我知道快到下莫村了,保姆的房子就在那里。但是我没时间停下脚步。还有两三公里的路。我只能看一眼马蒂娜房子的红色百叶窗,是关着的。我眼前浮现出那个醉汉的模样,希望再次见到他时能认出来。这一次我不能再逃走。
我终于来到了小丘陵,这里是一片荆棘林和灌木丛,还有椴木、刺槐、栗树和桑树。这里是小岛上最荒凉的地方。我记得杜瓦尔神父说过,海鸥湾(Crique-aux-Mauves)这个地名跟退潮时海滩上紫色(mauve)的花岗岩没有任何关系,“mauve”一词在古诺曼底方言里是“海鸥”的意思。我很快就发现了丘陵上方的谷仓。在一片荒凉的田野尽头,有一座被遗弃的谷仓。
10点17分。
不能再耽搁时间了!
我跑进院子里,大声喊道:“有人吗?”
没有声音。
突然我内心一阵恐慌,后背滴着汗。真像是恐怖片里的场景:荒凉的田野,海鸥的叫声,甚至还有乌鸦的叫声。
我对面就是谷仓的黑色大门。
“有人吗?”
还是没有声音。在走进谷仓之前,我看了一眼窗户,其实就是墙上的一个洞。谷仓里面很黑,我隐约看见一床旧毯子,几份杂志,一个煤气炉,甚至还有一台电视机。虽然整个谷仓散发出一股哈喇味,但是电视机还是很新,只是上面没有天线。我在想这人怎么看电视?
很明显,没有一个人。
我可以进去找找线索。
我正想转身,突然有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我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克制不住自己想逃的欲望,晃动手臂想拍掉后面的手。最后,我还是忍住了,慢慢转过身。
那个醉汉的脸出现在我面前,就快贴上我的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