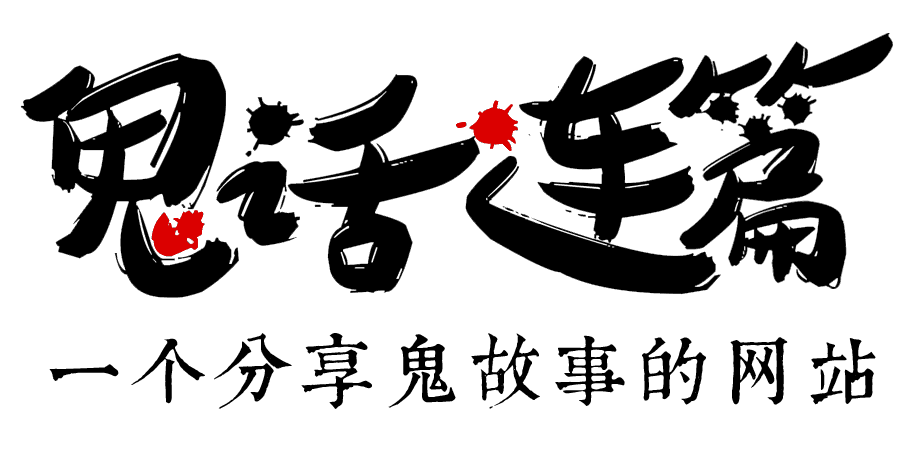2000年8月17日,星期四,下午3点3分
莫尔塞岛,监狱大街
我不擅长运动。然而,这个下午,我打破了个人纪录。在这个醉鬼俯下身来跟我说话之前,我拼了命地跑。这个酒鬼醉醺醺的,我想他应该追不上我……
只要他口袋里没有枪。
背都湿透了。我往前冲,没有回头。杂草淹没了我的大腿。我不敢低头看,我想腿上都是被杂草剐伤的血迹。
我的心跳得飞快。
我没法保证一直跑这么快。太蠢了。我可能会倒在路边,他会抓住我。我都快1年没跑步了。然而,我的腿还跑得动,这就是奇迹。但还能坚持多久?不管了,继续向前跑。
他还在我后面吗?
是的。
一直跑到路边。
路边?
是的。
前面200米就是马路边了。我现在不能倒下。
我再次听到了喇叭声、尖叫声和吵闹声。我的双腿已经麻木,也感觉不到杂草剐过的刺痛。
不能回头。继续走。眼前这段车流让我感到安心。
终于来到了马路边。
车子塞成一条长龙,走不动。
在司机吃惊的眼光下,我加速穿过了街道,来到了街道另一边。面前是一排汽车筑成的城墙,坐在车里开车的父亲们就是我的保镖。于是,我整个人放松下来。
我把中午吃的全部吐出来了,生菜、莴苣、火腿丁。还好没有碰隔壁的海鲜盘。一个6岁的女孩儿跟父母一起坐在车里,鼻子贴在奥迪80的车窗上,一脸惊讶地看着我。我拿着一张纸巾擦嘴,那个女孩儿还盯着我。
我看了一眼街对面,看不见那个追我的人。我应该甩掉他了。
这个恶魔是谁?逃犯瓦雷利诺吗?
有可能……
我得通知警察才行。
为什么要自找麻烦?我沿着监狱大道走着。车流不断朝着渡轮的方向开去,从那里才能回到大陆。
为了加重度假者逃亡的氛围,太阳也躲了起来,乌云密布。这是我上岛后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天气。一股狂风吹干了我湿透的后背。
我给自己打气。也许这个醉鬼跟逃犯没关系。也许是一个老水手,或者是个老乞丐,睡得晕晕乎乎被我吵醒。与其说他危险,不如说他可怕。他什么都没做,没有对我动手,甚至没有尾随我。
但我一个人还是害怕。
我来到了墓地。
高高的墙壁在路边围了100米长。旁边的车流让我感到安心。因为一旦进入墓地,我又是一个人。不过也不一定。
我推开铁门。因为生锈,铁门咯吱咯吱响,就像是恐怖片里的镜头。
我鼓起勇气走进去,但我立马泄气了。
墓地的高墙挡住了外面的车流。我走得很慢。墓地里阴森恐怖,外面的噪声越来越小。整个墓地就我一人。
我在想刚才那个家伙有没有跟进来,如果他跟进来,那我就被困住了。没人看得到我们。没人可以猜到墓地里发生了什么。我被困住了。
我不安地看了一眼身后,把铁门关上了。如果有人开门,我应该能听到。为什么这个人要一直追到这里?
墓地并不大,但我不知道父母的坟墓在哪里。我想转一圈应该比较快。
天色阴沉,太阳躲在云后面,愈发显得这个地方阴森恐怖。两棵高大的紫杉树,巨大的石碑,这些都是极佳的藏身之处。
我开始四处寻找父母的坟墓。墓碑上的日期让我迷惑。我在想人们从来不在墓碑上写这个人到底是几岁死的。然而,人们看到墓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计算生辰。
在每个墓碑前,我机械性地计算这个人的死亡年纪。
83岁。
67岁。
如果是60岁以下,我就开始想象这是什么悲剧。那些60岁以下去世之人的墓碑往往是保存最好的。
这也是我父母墓碑的情况吗?
谁在维护现场?是保姆吗?
绝对不会是蒂埃里和布丽吉特,除非他们花钱请人去做。我从没听他们说过。
接下来一排是儿童的墓碑。生锈的铁笼子,不到1米高。
4岁。6岁。3个月。
有些墓碑上面有照片。我浑身哆嗦,后背发凉。
我没见过比这些小笼子更恐怖的东西。我意识到我是第一次走进墓地。得快点儿找到父母的坟墓。
我加快了节奏,不再算死亡年纪,只看名字。但有些墓碑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被划掉了。
我加快了步伐。如果墓碑上写着“献给我的祖母,献给我的祖父”,我就赶紧走开。
我觉得自己卷入了奇怪的旋涡。墓碑上男男女女的名字,就像是一个死亡记录簿。我脑子里有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会更加简单。
为什么不可以呢?或者是按照时间顺序。
为什么如此杂乱?
我找不到父母的名字,心里愈发恐慌。我几乎跑遍了四分之三的小道。
如果我刚才错过了呢?
如果他们的坟墓不在这里呢?
我经常听奶奶说爸爸妈妈埋在这里,但那是很久以前了。
也许她在撒谎。
不……刚才的记者也提到了我父亲的坟墓在这里。还是说小岛还有另外一块墓地?也许吧。
越往前走,我就越绝望。谁在维护这块墓地?如果没人负责的话,也许过一段时间,人们会把这块地挪作他用。这也说得通。这块墓地的雕像残败不堪,很久没人维护了。10年了,我父母的坟墓不知道变成了什么样。眼前又是一条小径。
这是最后一条路。
突然我的眼睛定住了。
让·雷米&安娜·雷米
1959—1990;1960—1990
是合墓。
我的心碎了。
父母的墓碑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有人给整个墓碑泼上了红色的油漆。
在上面画了骷髅头、男性标志和十字架。
整块墓碑都被人亵渎过。
我面色苍白。
谁可以做出这种行为?谁会如此亵渎神灵?哪个疯子可以做出这种恐怖的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亵渎我父母的墓碑?
为什么他们的墓碑是整个墓地唯一被破坏掉的,在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里?
为什么?
我弯下腰。油漆好像还很新,应该泼了还不到两天。墓碑周围很多牌子也被弄脏了。上面写着:献给我的儿子。献给我的媳妇。献给我的姐姐。有一块牌子是圣—安托万协会成员送上的,让人想起修道院的石头造型。还有一块市政府送的牌子:献给莫尔塞岛最忠诚的人。
还有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刻着:献给我最好的朋友。
谁给的呢?是那个拉斐尔还是加布里埃尔,还是马克西姆?
我又凑近了点儿。
大理石墓碑上有一块玻璃里嵌着我父母的照片。
我再次感受到愤怒。
镜框里的父母很难辨认。有人用刀子刺穿了镜框,毁掉了整张照片,他们的脸都毁了。
谁这么恨他们啊?居然想毁掉他们的脸。
内心燃起无明火。
这是为什么呢?
今天一整天,我遇到的人都在跟我说我父亲是个好人,值得尊敬的人。但是这里有人亵渎了他的坟墓,毁掉了他的照片。
我想到了工地上死去的工人。
为什么是在10年后呢?今天,在我回来的这天?我的父亲真的是保姆描述的那样值得尊敬的人吗?这一次又有人撒谎吗?我忠诚的父亲,模范父亲和丈夫,小岛上最让人羡慕的一对夫妻,死也没有分开,葬在一起……这是人们讲给我的神话故事。因为只有我母亲一人躺在这里。我父亲睡在别处!
我知道。
他没有睡在这里!他在小岛上开着一辆白色卡车,逍遥自在。
那个在我母亲眼皮底下调情的红发女孩儿呢?
她现在怎么样呢?
她跟我父亲的失踪有关系吗?
这一切不过是假象。所有人都在撒谎。
我父亲到底是谁?
墓地的铁门突然咯吱响,打乱了我的思绪。
我转过头。
天空依旧阴暗,墓地气氛阴森,我还是认出了他的身形。
就是他!
那个醉鬼,没有牙齿的水手。我没有在农田里吵醒他,也不是随便就碰上了他。
他在跟踪我。
他要找的人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