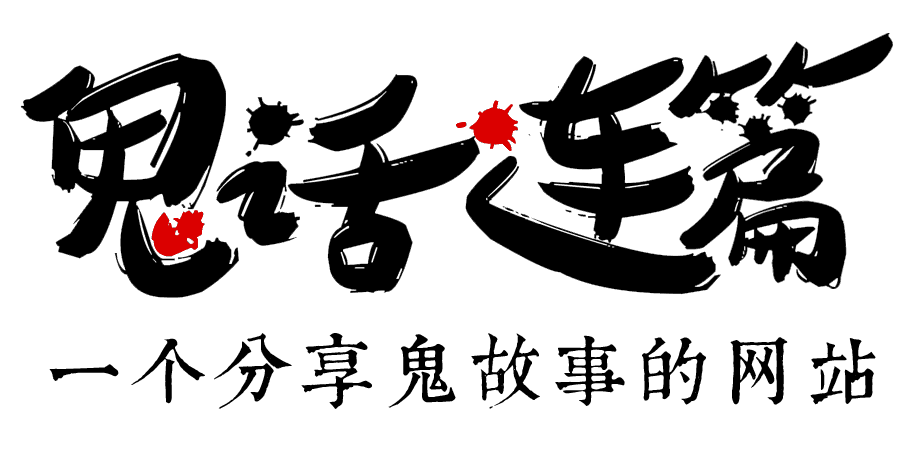2000年8月17日,星期四,12点1分
莫尔塞岛,圣—阿让大道
我朝圣—阿让的方向走去。港口离这里还有1公里远。我本来是站在小岛地势比较高的一边,但这条路的斜坡上全是榛树,看不清眼前的全貌。很多车从我面前经过,比以往更塞车,都是开往港口方向的。就像是小岛最东边的“海豚营”一下子把度假者全部赶跑了似的。
源源不断的车流从我面前经过。我爬上了3米高的斜坡。经过这片农田,就可以到达修道院大街,也就是红宝石湾对面。那里人烟稀少。我在小路上艰难地前行,沙石、尘土、野草阻挡了前路。然后我来到一片松树林。内心坚定的我在松树林的影子下走着,踩了一脚的沙。
还有300米就可以到达修道院大街,还有40米就是红宝石海滩。马上就能看到无边无际的海滩了。
前方到处都是警察的车。
不止一两辆。整个停车场停满了警车,就像电影里一样。
一条长长的橙色带把整个沙滩围起来。十几个人在警戒线后面观望。潮水拍打着空荡荡的海滩。几个穿着蓝色制服的警察就像是蚂蚁一样走来走去。他们交头接耳,蹲下来勘查现场。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有人溺水了,但眼前这幅慌乱的景象又像是一场游泳事故。
是鲨鱼吗?
我笑了。
这座小岛上有两个逃犯。这就是原因。我内心涌上一阵恐慌。这座小岛这些天来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像是某个大事件要爆发了。仿佛这座天堂小岛快要塌落成碎片。
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继续朝圣—阿让走。这条路比海鸥湾更加堵,车子只能龟速前进。看到车子里面的装备,我感觉大部分度假者都打包好了所有行李。
为什么在这个星期四离开呢?在大白天的中午?头顶烈日?
真是太奇怪了!我想象渡轮口肯定是大塞车。幸好单车道畅通无阻。我在车流尾巴看见了法国2台的采访车。肯定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这些大陆的记者才会这么快赶来。
我到了圣—阿让市政府。
好奇怪,怎么这么安静?除了刚才沙滩上看热闹的一群人。小岛上唯一的电话亭位于村子的中心广场——1908-5-20广场。我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我走进了电话亭。
塞了一枚硬币,按下奶奶马德莱娜的号码。
响了三声之后,奶奶接了电话。
“是奶奶吗?我是科林。”
奶奶有点儿吃惊,但也很开心。
“科林,你还好吗?你从营地打电话给我,我真开心。你的舅舅和舅妈说那里不能用手机。你过得开心吗?帆船好玩吗?”
我等她说完这些家常话,接着问:
“奶奶,爸爸有双胞胎兄弟吗?”
奶奶在另一头没话说。她的小心脏哦……她还是缓缓开口:
“你在说什么啊,科林?”
她被我的问题吓到了。刚才是测试。我重复问道:
“爸爸有双胞胎兄弟吗?”
她开始整理思绪。
“当然没有!你在干吗?当然没有!你为什么问这么蠢的事?”
我决定向她坦白。
“我昨天看到了爸爸,他还活着,就在小岛上。他在港口开小货车。”
她的反应也是我害怕的。她为孙子的心理健康担心。
“我可怜的小科林,你别再瞎编故事了!不要这么疯疯癫癫。你在港口看到的不是让,也不是他的双胞胎兄弟。你爸爸死了。他是独生子。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可以对天发誓。你只是看到一个长得像他的人而已。”
我很想大喊:不,我不相信。
奶奶继续说:
“你不应该回到那个不幸的小岛。我一开始虽然同意了,但现在我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信息。她的回复很真诚。双胞胎兄弟这条线我自己都不太信。看来现在是死胡同了。
我安慰了一下奶奶。
“你说得对,奶奶。肯定是长得像他的人。我只是想确定一下。别担心。”
奶奶还在追问我:“你确定吗?你还好吗?”我最终挂了电话。
我看了一眼手表。
现在是下午1点7分。
我下午4点要回到营地……我饿了。一夜无眠,早上醒来时又受了惊吓,我从昨晚开始就没吃,除了保姆的几块猫耳朵饼干。
我观察了一下四周,几乎没人。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尊红衣主教马萨林雕像,直视前方的港口和大海,下巴上的小胡子惟妙惟肖,鬈发垂落在肩膀上,双手叉腰,面对小岛的嘈杂表现出淡漠的样子。
我最终决定在大科莫兰餐厅吃点儿东西,这里有整个村子最美的露台。为了抓紧时间,我点了一份沙拉。我观望了露台四周还有港口,担心杜瓦尔神父、斯蒂芬妮或者悠悠会突然出现,同时看了一下圣—阿让的女明星们的表演。现在岛上不太安宁,估计杜瓦尔神父和其他人会比较警觉。我想象他们看见我独自一人在露台,手里还拿着啤酒是什么反应。
大科莫兰的露台几乎没有客人。
我觉得应该是海啸袭击了小岛。等会儿我要去哪儿呢?必须去墓地。10天了,我一直在想这件事。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去父母的墓地,就像是朝圣一样。也许是因为站在父亲的墓地前,我才能进一步坚定父亲还活着的信念。
我点的沙拉端上来了。花了8.5欧,只有三块萝卜、十几块火腿丁和小山一样的绿色生菜叶。真够坑的!这里就是罪恶之岛。离我最近的那张桌子坐着个老帅哥:老鹰一样的眼神,帅气的夹克衫,手机贴在耳边。他一个人吃了一盘海鲜拼盘,外加一瓶已经喝了一半的白葡萄酒。我简直无法想象他那盘龙虾的价格。
尽管如此,我在偷听那个老帅哥在手机里对人咆哮。
“不是的,我不在红宝石湾那里。我在那里干吗?你瞎说。那里什么人都有。是的,电视台、广播台的人都来了。那里大塞车。我不在那里挖内幕了。”
我注意到他手里的圆珠笔上面刻的字是“小岛人”。我马上得出结论,他原来是个记者,想法很周全。
记者继续讲电话。
“别担心,我有我的路子。我有线人……”
他突然哈哈大笑,把港口的海鸥吓跑了。
“今天早上我已经放出了重磅头条!引起了小岛大恐慌!我本来很期待市长和监狱长看到头条时大吵一架,看来力道还不够狠。如果所有游客都跑光了,那么我的报纸也没有读者了。”
双方都安静下来。
手机另一端给他提了个问题。记者趁机喝光了酒杯里的酒。
“不不,是出埃及记。营地的人都快跑光了。估计塞了上千米。渡轮今天已经往返第四趟了。据说还要把泽西岛的渡轮也派过来。这次撤营很匆忙,从早上9点开始。你想想,孩子们还没来得及在沙滩上搭沙堡。”
他再次发出狂笑。
“该死,关于疯狂马萨林,我还有10页料没爆出来,等着吧,我先藏着。”
我想问他几个问题,错过这村没这店儿。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匆匆吃完了沙拉,在等待机会。但是那个老家伙还在打电话,都打了快45分钟。记者的工作就是聊个不停吗?这是我感兴趣的职业!
他继续说:
“你明白吗?早上10点,报纸就卖光了,这是8年来头一次。现在我可以休息会儿。今天早上一直有人要采访我,法国新闻台,欧洲1台。你也许还可以在法国信息频道上看到我出镜。知道不?得好好利用一下,不是吗?明天的头条也许是其他事,没关系。我就把疯狂马萨林的故事抛出去,可以吧?好的。就像你说的,我得去找内线了。”
他最后一次开怀大笑。
“再见!”
终于讲完了。
我没给他缓气的空间。他甚至没来得及再吃一口菜,或者喝上一杯。
“您是《小岛人》的记者吗?”
“是的。”
他看起来并不吃惊,甚至是微笑友好的。
“小朋友,我可是主编。”
我习惯了。我开门见山地提问:
“不好意思,我在找资料。关于10年前莫尔塞岛发生的一件事情。跟考古学家让·雷米有关。不知道您还记得什么吗?”
记者脸色变了,长时间地看着我。我在揣摩他的反应。小岛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两个逃犯在外,还有红宝石湾发生的事件。大家都在谈论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只有我提起了10年前的幽灵。
与主题无关吗?
不见得。
主编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毋庸置疑,他是个好记者。他知道如何制造悬念。他本来可以骂走我,但是他并没有,他凭本能察觉到有猫腻。他知道如何让对方上钩。
“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呢?”
“我是让·雷米的儿子,我参加了杜瓦尔神父组织的夏令营。”
他趁机吃了个牡蛎。
“让·雷米的儿子。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啊!一具尸体,一个故人。”
他吃下了第二个牡蛎。
“不好意思,但我记得你当年还是小豆丁。你的名字是?”
“科林。”
“科林,好的。小朋友,我现在不能跟你说。今天有点儿混乱。但是你可以随时来《小岛人》报社。我的电话号码15年来没变。你会知道关于这件事的所有细节。”
我看着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你要知道,那真是个狗血的故事。你父亲真是运气不好。他很勇敢,但不走运。我其实很想相信他,但是他的手下太不靠谱了。他的哥们儿马克西姆·普里厄,还有他老婆的弟弟。他不应该相信他们的。他们就是瞎搞。你父亲太单纯了,特别是跟钱有关的事……他们骗了他。他不属于这个罪恶之岛。他的理想主义威胁了这个小岛上其他人。”
我没多少时间。我想知道最终答案。
“您没有怀疑过他的死亡吗?”
记者有些吃惊,还带着一些犹豫。
“不,没人提过这个问题。他留下了一封诀别信……人们找到了他的尸体……他无法背负三个人的死亡,所以可以预见……”
我继续追问:
“您再也没有在小岛上见过他吗?我是说,活着的他。”
《小岛人》的主编神情充满了慈悲和怜悯,这正是我讨厌的。他在担心我的心理状况。
“当然没有啊,我的小朋友。我15年来进进出出这个小岛。你的父亲跟你的母亲一道安葬在小岛的坟墓里。你母亲当年可是小岛最美的女人,你父亲运气很好。我很喜欢你的父亲。他是个忠诚的人,一个有原则的人。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小伙子。你父亲死得有尊严。”
记者举起了他的酒杯。
“敬你的父亲,科林。他应该喜欢这种酒。来一杯泽西岛的白葡萄酒。盎格鲁—诺曼底岛上最后的产酒区。”
“可是……我昨天在港口看见了他。”
“你的父亲在莫尔塞岛上很出名。如果他在小岛上散步,他会被马上认出来的。所以相信我,只是长得像他的人……”
他的论述打破了我的幻想。但我还是坚信,我不能放弃。
“你说我父亲是理想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他放下了杯子。
“这是个很长很复杂的故事……你最好读读那个年代的文章。现在我没时间。这件事跟一个房地产商‘欧洲建筑’有关,还牵涉到国家文化遗产修道院、你父亲的协会成员,还有圣—阿让市政府,具体说跟施工许可证有关。”
突然他停下来,好像哪里不对劲,然后他再次睁开眼睛。
“砰砰砰!”他停下来,“施工许可证。小家伙,你刚刚给了我灵感。”
我不太明白。
“现在可以解释清楚了。”他继续说,“一开始我以为瓦雷利诺只是涉及公务采购受贿案。现在如果跟嗜血者工地事故联系起来就说得通了,他当时在市政府做实习生。”
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
“小家伙,你真是从天而降的礼物。你的父亲明天就上报纸头条!”
从那一刻开始,他对我失去了兴趣。他重新拿起电话,给一个秘书打电话。
“是的,关于瓦雷利诺,那个幸存者。我在找明天的头条,连全国媒体都找不到的爆料。他的贪污案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炒作的是嗜血者工地事故。我知道这没什么直接联系,但是我们可以暗示点儿什么。他当年也在市政府做实习生。你最好帮我把资料找出来。我马上到。”
他下一刻就出发了,盘子里还剩一半的海鲜。我还饿,但还不至于可怜到去吃剩菜。
我看了一下表。下午2点30分。我要在4点前回到营地。去到墓地至少需要三刻钟,那里是小岛的北部。然后一刻钟回到营地。
太阳和天上的云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微风吹过,要变天了。
我有点儿头疼。要成为英雄还得继续努力!喝了点儿啤酒我继续上路。再一次来到修道院大街前。我走得比那些车还快。远处,我看见了警示灯。
出埃及记!
记者没说错。度假者几乎都是一副仓皇出逃的模样,车子里堆满了行李。后备厢也是满满的。孩子们因为掉落在营地的玩具和提前结束的假期而哭泣。大点儿的孩子趴在窗户边看着警察们走来走去。
这一切只是因为两个逃犯吗?
记者提到了一具尸体,还有让—路易·瓦雷利诺这个人。两个逃犯之间发生了冲突,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还在逃亡中。我明白记者在逃犯和欧洲建筑这家公司的工地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细节有待进一步澄清。
对于我来说,目前最关键的问题,也是记者也无法解答的难题:
为什么我是莫尔塞岛上唯一一个认出了我父亲的人?
沿着修道院大街走了1公里,冒着热腾腾尾气的汽车散发出呛人的汽油味,保险杠贴着保险杠,这一切都让人难以忍受,感觉有点儿恶心。我决定穿过农田抄一条近道,那里靠圣—安托万修道院北边一点儿,走到尽头就是监狱大街,正好面对墓地。
刚刚离开大街,我发现路上只剩下我一人。汽车愤怒的喇叭声,被从农田吹向大海的风声给淹没。
我越走越害怕。
一种无法形容的害怕。
是跟其他度假者一样,一种莫名的害怕吗?
那条通往海滩的路还不到150米长,每平方米就站了一个警察。逃犯的事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沉重。杜瓦尔神父建议我们绝不要独自出行。因为纠结于调查工作,我就忘了最基本的安全提示吗?我一个人在如此大的小岛上走着,还有一个逃犯在外……谁都可以躲在路边的荆棘林里。我走过一片野草丛和一片废弃的葡萄园,草丛很高,连1米前的景色都看不清。
其实就算逃犯藏在农田里某个地方,他们应该也不敢出来。我试着唱军歌,给自己壮胆。
在炮火下……
我一边唱一边走。就像是在石头上走路,试图用声响赶走藏起来的响尾蛇一样。
穿过枪林弹雨……
如果逃犯在前方,他们应该听到了我的歌声,趁机躲了起来。
我们走向胜利……
我看起来像个十足的笨蛋,一个人在农田里唱军歌。刚才那口啤酒还让我反胃。我应该走大路的。
这是最漫长的一天……
我突然听到了声音,就在正前方。
我马上想到了某种动物。于是,我安慰自己,装作没事一样继续走。如果是记者口里的逃犯瓦雷利诺,如果他知道你注意到了他,你就死定了。你唯一的机会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继续唱歌。尽管脑子里一团糟,但是我的歌声并没有发抖。也许是一对情侣在做爱。我完全没有兴趣去证实。
在我面前,一棵树的枝叶在晃动。
有人藏在那里!
继续唱歌。不要扭头。不要做出回应。
我继续往前走。
保持一样的节奏。监狱大道应该在不远处。
我的脚步越来越快。
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感觉到潜在的危险。一边走一边打寒战。我听到了跟我的脚步声形成回声的另一个脚步声。
有人喘着大气。
就在我后面!
我继续往前走。
就像是什么都没听到。
后背在滴汗。继续保持冷静吗?呼吸声越来越近。我低下头看脚底,一个影子出现在我影子后面。
我的喉咙哽住了。
我吓坏了,也许接下来会有双巨大的手扣住我的肩膀。影子越来越近,叠在我的影子上方。没法反抗,我回过头。
尖叫出声!
我面前是一个恶魔!他牙齿脱落了,衣服破破烂烂,头发花白。就像是海盗电影里喝醉的水手。他不是悠悠假装的。是一个真正的酒鬼。
他弯下腰,伸出一只脏脏的手想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