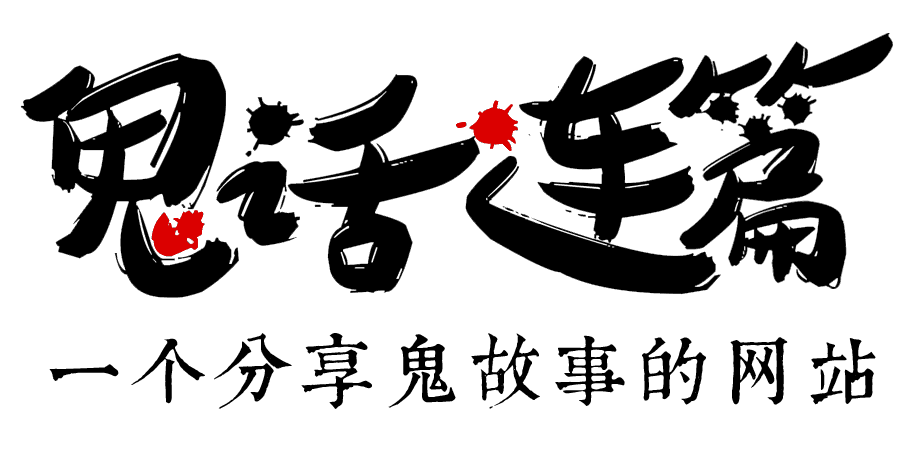2000年8月17日,星期四,8点45分
莫尔塞岛,半岛营地
没有脸的僧侣离我越来越近。我差点儿叫出声来,直到我听到后面一堆傻瓜的叫声。僧侣脱下了帽子,悠悠的脸露了出来。
“起来,小毛孩儿!主教在等你。其他人都在大厅里等着。”
他在我面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离开了。
“第一个睡,最后一个起。”阿尔芒在外面说道,“科林,你比猪还能睡。”
很明显,他在帮我找借口。事实上我几乎一整晚都没睡。我走出帐篷,还是迷糊的状态。雨果是老营员,他连续参加了5年,给我们讲了恶作剧真相。
“每年都是一样,休息的那一天,如果不玩帆船,他们就玩这个游戏。他们这一套玩得很熟练。服装是旧了点儿,但是总能吓到新人。他们让老人不要告诉新人。很好玩,不是吗?”
“然后呢?”阿尔芒问道。
“我们组成小分队,花上一整天去寻找宝藏。拿上一张羊皮纸,上面是小岛的地图。每个人路线图的颜色不同。”
“太好了。”马迪叹了口气。
斯蒂芬妮化装成修女。杜瓦尔神父穿着红袍,别人以为他是主教。
“这个杜瓦尔神父看起来有点儿太夸张了吧。”阿尔芒跟我低声说道。
主教和他的两个手下给我们做了一场很出色的演讲。我们今天要去寻宝,要展现出勇敢、狡猾、灵活和机智这些品质。他们给我们发了一张彩色卡纸的路线图,上面还有十几个问题,有线索也有陷阱。三到四人组成一队。
真是绝佳的机会啊!
马迪、阿尔芒和我顺理成章组成一队,互相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最佳组合,我们三人是最佳组合!”阿尔芒大喊。
“是的。”马迪确认。
阿尔芒看着这个比他还高30厘米的女孩儿。她戴着一顶鸭舌帽,一副太阳镜,穿着一件宽大的T恤。
“为了让我们增加信任,可以来个法式湿吻吗?”阿尔芒对马迪说。
“你可以去吃屎了!”
阿尔芒耸了耸肩,想在马迪的太阳镜里欣赏自己的倒影。
“我开玩笑的,大姐。你才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大胸和有脑子的……你正好缺这几样!”
马迪做好了格斗的准备。
这下子不可收拾了!
阿尔芒穷追不舍。
“我们两个男子汉,”他看着我说,“需要的是一个美女搭档,一个真正的女孩儿。”
“让她来使美人计?”马迪说。
我开口解围。
“不要吵架!”
“如果你昨晚跟我说了,我就会在深夜潜入女孩子的帐篷里,我会在她们的床上尿尿。”阿尔芒继续说。
马迪明白阿尔芒也知道这件事了,这个浑蛋会搞砸一切!幸好马迪还算靠谱。她意志坚定,不会想东想西。
“真正的女孩子不会管不住嘴巴。”
生怕阿尔芒又说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话,我赶紧打断他。“好了好了,我们三人一组,第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先走。”
我们带上食物和地图,从营地走出来。天气有点儿凉,但今天肯定是个晴天。微风习习,我闻到了碘伏的味道,还听到高处的猫头鹰低沉的叫声。
多么美好的一天。
阿尔芒接下来的话打破了美丽的意境。
“你真是恶心,科林。”他抱怨道,“我要跟她在一起待一整天,就是为了帮你打掩护。”
阿尔芒想到要跟马迪待一整天就不开心。
“这可不是蠢事,阿尔芒。”
我越来越欣赏马迪的成熟和决心。她虽然是个狠角色,但让人放心。
“就是蠢事。科林,你着魔了,你以为在拍电影,你就像是《眩晕》里的男主角。”
“什么电影?”马迪问道。
我叹了口气,阿尔芒找到借口来发表长篇大论了。
“《眩晕》(又名《迷魂记》),法语版名字是《冷汗》。希区柯克的大片。我给你说个概要。前警察被雇佣来监视一个女孩儿,她最后自杀了。他怪自己,甚至变得抑郁。突然,他遇到了一个女孩儿很像死去的那个女孩儿,他把她当成了她。他让她打扮成那个死去女孩儿的模样。为了让她死而复生。你明白了不?”
阿尔芒卖了个关子,我知道。马迪上钩了。
“后来那个女孩儿是她吗?”
“哪个她?”阿尔芒好像没懂。
“第二个女孩儿。真的是另一个女孩儿吗,还是没有死去的第一个女孩儿?”
阿尔芒嘴巴里嘀嘀咕咕。
“是同一个女孩儿,是演戏来着,她一开始就没死。”
我内心窃喜。谢谢你,马迪!
我们在十字路口分道扬镳。他们往右边的监狱方向走去,我抄小道往修道院走去,前方200米就是。在跟他们分离之前,我鼓励他们:
“加油,小沙弥们,要展现出勇敢、狡猾、灵活和机智这些品质……你们俩待一天说不定会擦出火花,我相信你们会赢的,晚上回来的时候要挖到宝藏哦!”
阿尔芒色眯眯地笑了,马迪朝他竖了一根中指。阿尔芒扭过头,对我说:
“狗屎!你也必须帮助我们。我们沿着红色的路线走。如果你发现了什么线索……”
我朝他们挥挥手,然后走上了修道院的小路。
“你自己也小心点儿。”马迪在远处叮嘱我。
我很感动。
终于一个人啦!
我走在前往圣—安托万修道院的路上,试着整理大脑里的线索。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我今天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做这些事:参观修道院、找到保姆、给奶奶打电话、去墓地看看父亲的坟墓。时间太紧张了。
我走在小路上,大概还有30多米到修道院。圣—安托万修道院的大十字架矗立在天空中,抬起头就可以看见。
从昨晚开始,我内心充满了力量。曾经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少年,在学校也不算出众的学生。语文还不错,数学和其他科目都很糟糕。至于体能方面,也不算优秀。中等身材。外形也不算可爱的类型,至少我自己不觉得。而且我在女孩子的眼里也看不见火花。
平庸……一个十五六岁平庸的男孩儿,有比这更糟糕的吗?
我尤其讨厌周围的规章制度。
幸好,还有孤儿这样的身份做挡箭牌。这可是我的武器,我的绝招!可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6岁失去双亲。每一次我讲完自己的故事,周围人的脸色都变了。我的犹豫在他们眼里变成了神秘,我的内向腼腆是很好的面具,我的善良是抵抗失望的内在力量。
我是比较保守的类型,甚至可以说是拘谨。我并不经常讲自己的故事。在中学,我遇上过两个有好感的女孩儿,每一次,孤儿的身份都派上了大用场。最后一个女孩儿罗琳算是非常优秀的,居然愿意跟我约会。我给她讲了我的故事。当然这段关系没有持续很久,看完一部电影,她就把我甩了。但是无论如何,我还是跟她交往过,不是吗?
孤儿的身份被我拿来做幌子,这样做很令人震惊吗?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一个女孩儿或者一群男孩儿面前讲述我的故事,可以让我纾解情绪。
我没有讲太多细枝末节,只讲到了父母去世。
但我从没有跟蒂埃里和布丽吉特讲过这些,也没有跟其他大人讲过,我想我这样做……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哀悼会。这是我与父亲告别的方式。我最终成为另一个人,一个在学校里被人们议论的对象:“你不知道吗?科林他在6岁时失去了父母。是的,父亲和母亲,两个人!”
法国版的哈利·波特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在10年后回到莫尔塞岛。
不是出于怀旧。
更多是出自虚荣心。
去找到新的线索,新的逸事,未编辑过的参考资料,好给我的个人传奇添油加醋。6岁的时候,我祈祷一切能恢复正常,没有阴影,没有神秘事件。而我现在15岁了,想法正好相反……现在我身边只有谎言,真相在小岛的某个地方等着我。我等了快10年。
路的尽头正对修道院废墟,旁边有个小停车场,停了三辆车。大十字架落下一个巨大的影子。才上午10点就已经很热了。停车场尽头,有一排木头柜台。柜台前方摆放着几张明信片和《小岛人》。
我抬起头。柜台的女孩儿是个大美女啊!
我是个比较挑剔的人……但是这个美女让人目不转睛。
金发马尾辫,小小的鼻头,大大的微笑,蕾丝边短上衣,晒到黝黑发亮的皮肤,哇哦……这可是我最爱的类型。但我得集中注意力干正事!
我摆出一副乖巧懂事的表情。
“一张门票,谢谢。”
“给,你是大学生吗?”
她有点儿口音,我觉得她应该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边的。她把我当成大学生,其实我后天才满16岁。
“不是。”我脸红了。
她笑了,把票递给我。
4欧元。
居然不是免费的,不就是废墟嘛!她应该是考古学的大学生,把我当成来参观废墟的青少年。
我看了一眼《小岛人》,巨大的红色标题:
莫尔塞岛大恐慌:两名逃犯在外!
这个标题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眼球。我立刻把这个新闻跟昨天监狱附近的警示灯联系起来。头条标题让人想了解更多内情,但是得买一份报纸才能知道后续。幸好杜瓦尔神父今天早上还未得知这个消息,不然他不会放我们出门。
在修道院废墟里,我只遇上了两对情侣。一对退休的,还有一对年轻人。老夫妻看起来像是老师。男人戴着眼镜,穿着凉鞋,趴在地上研究石头,女人手里拿着蓝色的导游册。我在阴凉处散步。
废墟非常无趣,不过是几块石头堆在另外一些石头上。我来到一间房,他们称之为教士会议室,也是修道院保存最好的房间。门口的牌子上面有文字说明。这间房是僧侣们唯一可以说话的地方。我记得悠悠今天早上说过教士会议室这个词。
我对这些废墟不感兴趣,就像是荒废的建筑工地。还设置了栅栏不准通过。招牌上写道:
危险,禁止入内!
我对这些细节完全没有印象。不过我记得这里的灰尘、石头,跟那段视频和照片上的颜色一样。
如此熟悉的背景,但跟我要探究的过去毫无关系!这些说明文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修道院于1337年建成,它属于本笃会,后来由马萨林主教重建,直到大革命前,僧侣们还在从事葡萄酒业务……
突然,我心里滋生出一丝愧疚之情。我的父母热衷于挖掘古迹,但我对此毫无兴趣!
我有何用?
我怀疑这片废墟最有趣的部分藏在栅栏后面,那里是地下隧道的入口,真正的遗迹所在。我的记忆也许掩埋在那里。我琢磨着溜进去。反正游客这么少,他们也注意不到我。除了门口的瑞典女郎,我没看见任何保安。
我低下身子,穿过栅栏。地面逐渐往下沉,形成一块洼地。没人注意到我。但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我随时可以呼叫。瑞典女郎会来救我,然后给我做人工呼吸。
洼地尽头是深深的草丛,荆棘和荨麻刺痛了我的腿。我踩在切成不同形状的石块上,慢慢往前走。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远处,我看到一个外形模糊的门,被几块看起来摇摇晃晃的石头围住,这里应该就是地下隧道的入口。
我向前一步。
我把头伸进洞里,什么都没有,即使是大白天也什么都看不见。隧道看起来快要坍塌。几步就走到了黑暗处。我犹豫着要不要进去,可是没带手电筒。就算我想逞英雄,也什么都看不见。
我是个多么业余的冒险家!要在这样的隧道里探险真是太滑稽了。我只能原路返回,这一次避开了荆棘。脚突然踩到了草丛里的金属板。我低下头,发现一个珐琅材质的旧牌子,之前被草丛盖住了。我仔细看了看上面已经生锈的字样:
圣—安托万修道院考古遗址
1982年4月5日
让·雷米&安娜·雷米
圣—安托万协会
就这点儿线索。
一个标识,一块生锈的牌子。我心中有个想法,想把这一片废墟摧毁。我的父母在这片废墟度过了一生。他们在这里挖掘古迹,然后进行分类和整理,后来却死了。
为什么?
为了这一片废墟值得吗?
一个被幽灵造访的地方。几个迷路的游客,他们从没听说过我父母的存在。
让·雷米&安娜·雷米
他们的名字没有写在修道院的入口处,也不在4欧元的门票上,也不在海报上,更加不会在蓝色导游册上。只刻在一个被人遗忘的生锈的牌子上。
真是浪费!
这些石头对我父母来说这么重要吗?值得他们为此献出生命?
沉思了几分钟,我离开了修道院,心情低落。
柜台的瑞典女郎戴上了眼镜,没有抬起头看我。
这一切都让我心烦意乱。
我得冷静下来,实施下一步计划。
我今天的第二个目标是找到保姆。我努力回想,她就住在修道院附近,北边一座独门独户的小房子。早上母亲把我送到保姆家,中午保姆马蒂娜带我回到修道院跟大家一起吃饭。下午和晚上也是如此。从修道院到保姆家,一天往返多次。
当年我6岁。
重归故里,应该能回想起很多事情。
经过修道院,我下意识地往右拐。200米远,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虽然我完全没印象,但是我还是下意识地往右拐。500米尽头,看不见任何房子,只有草堆和一段废弃的小路。11天来,斯蒂芬妮教我们认识一些野生植物,比如:大戟,兔尾巴草,野生萝卜,拂子茅。
但是现在我没有时间上植物课。我走错路了!更远的西边是一个小海滩。
只能折回去。
回到十字路口,我朝圣—阿让的方向一直走。拐弯后,来到一个小村庄前。三栋小房子依次排开,深色的苔藓爬满了厚厚的花岗岩矮墙,斑驳破碎的感觉就像是老人斑,淡紫色的锦葵让外墙焕然一新。还有这座小岛独有的红色百叶窗。
蓝色的招牌上写着:
下莫村
这里是我熟悉的场景。
应该就是这里了。
我的保姆叫马蒂娜,但我不记得她的姓。第一个信箱主人叫米歇尔,第二个叫贝尔纳,第三个信箱上刻着:
马蒂娜·沙马尔
就是她了!
灰色小房子的花园被一块木板拦住了,木板当然也是红色的,跟百叶窗一样的颜色。车库前有一排陡峭的滑道。花园深处养着母鸡。
回忆如潮水涌来。
我小时候在车库的滑道上跑过吗?眼前这一切比我想象的要小。
一条狗在门后狂吠。一只手颤颤巍巍拉开了窗帘。我看到脏脏的窗户后面一张皱巴巴的脸。
一直在抖动的手打开了窗户。
“有事吗?”
是她!我确定,虽然我不知道为何自己如此确定。
她的声音,她的手势,还是整个氛围?
虽然没有认出细节,但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很熟悉。我对房间内部印象深刻,我可以准确地找到客厅还有卧室。
“有事吗?”她再次问道。
我在犹豫。
喉咙被卡住了。
我要喊什么?
夫人?保姆?马蒂娜?
将近10年没有这种感觉了。
最后,我开口了:
“是我,科林。科林·雷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