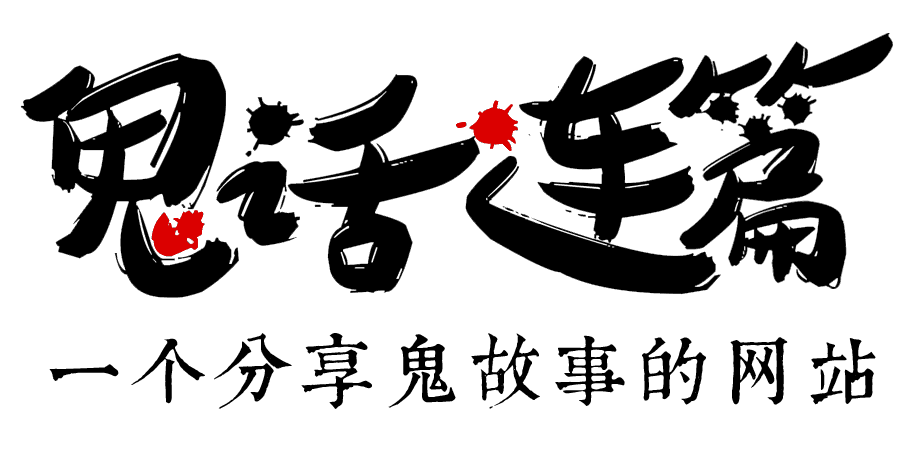2000年8月16日,星期三,下午5点10分
莫尔塞岛,修道院大街
“闭嘴!”在阿尔芒开口之前我就吼了他一句。
还好阿尔芒很快就明白了。他不再坚持,跑去逗弄其他人,心情好得很。
我得赶紧躲起来!我机械地跟在一群人后面,收拾帆布,拿回干衣服,穿好衣服,步行出发去营地。离开港口,穿过圣—阿让的1908-5-20广场,经过马萨林雕像,走过红色百叶窗小路,直到村子的出口。同样的路线,同班人马,就这样走了10天。
我甚至可以闭着眼睛走这条路。
父亲居然还活着!我脑子里理性和感性开始打架。
一边是感性思维,完全无法理解现状。所有人都跟这个孤儿说他父亲死了……结果10年后他还活得好好的!真是混账。
另一边是整个事件的逻辑推理。
我一面走一面理清思路。有规律的步行有助于思考。不,没有非理性的部分,一切都符合逻辑。我妈妈最后的话就是预言:某一天,你会与他相遇。
她是什么意思?
是说他去了远方?还是说他没死?
如今,这一切都清楚了。首先是我内心的感受。我6岁时没有大哭大闹,10年来没有悲愤之情。一般来说,一个小孩被告知他父亲去世后,至少会流泪、发狂,或者陷入抑郁。这些年来我这种冷漠的反应该如何解释呢?我早就知道他们在撒谎。父亲其实还活着,他在等我。
也许,这一切是我想象出来的。这也是让我消除罪恶感的方法,是我潜意识的产物。
在我面前,悠悠和三个年轻人开始哼唱《最长的一天》,与其说是唱歌,还不如说是踏着步子哼调子,跟随节奏使劲踩在泥泞的小路上:“在枪林弹雨下……我们走向胜利……因为这是最长的一天。”这些白痴一边唱着最俗气的调子,一边大踏步。悠悠走在最前面。他们不记得歌词,就哼着小曲。
我把自己封闭起来。
躲在属于自己的黑色气泡里。
我没亲眼看见父亲死去,没见到他的尸体和墓碑。我甚至不知道他的死因。因为没有葬礼,这些年来,我穿街走巷寻找父亲的踪迹,不想接受现实。我在很多书还有网上看过关于葬礼的资料。我不害怕死亡这件事。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我的信念……因为我父亲还活着,这些年来其他人欺骗了我!
我们离开了圣—阿让市中心,沿着新区溜达。全新的小别墅,只有两层楼高,都长一个样,跟莫尔塞岛的农场、村子还有圣—阿让的房子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现代化的阁楼在我看来非常平庸,既脆弱又神圣,就像是给游客们设下的陷阱。囚禁游客的秘密监狱。几个小时前平淡的风景如今充满了神秘感。
从圣—阿让出来,穿过修道院大街就是延绵5公里的荒野。为了避开车辆,我们走在自行车道上。草丛呼呼的风声让我恐慌。远处是圣—安托万修道院的十字架,杜瓦尔神父说它位于一个小土堆上。十字架顶的天空开始变暗,给周边的风景增添了恐怖片的氛围。其他人没有注意到我如此阴暗的想法,开始哼唱《大逃亡》的旋律。
越来越阴暗的天空揭开了小岛隐藏的另一面。荒野上的生物,僧侣的幽灵。我知道这块荒野下方就是地道,把圣—安托万修道院和马萨林监狱连接起来,直达圣—阿让港口,还有红宝石湾和海鸥湾。这就是父亲当年挖掘出来的地下迷宫。悠悠和其他少年的欢呼声还有靴子声惊醒了地下沉睡的生物。刚刚经过的新建别墅区也跟这块神圣之地格格不入。
有些事情的节奏被打乱了。
如今这座小岛已不是我父亲当年的小岛,亦不是我童年时的小岛。然而,它随时准备好换个样子出现在我面前。
就像是我父亲。
岔道口指向大海。前方300米是小岛最美的沙滩——知名的红宝石湾。这个名字很奇怪,因为海滩周围全是绿色的灌木丛。
红宝石湾?
我第一次想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取个这么奇怪的名字?为什么是红色?为什么以前的人会这样取名?红宝石湾。是撞上暗礁的水手们流出的鲜血吗?欧洲最大的潮汐退潮后,露出上百块礁石。斯蒂芬妮试着教会我们那些岩石的名字:浪花石、沉睡者、三兄弟、男童……我完全记不住这些名字,它们就像是天空中的星宿一样纷繁杂乱。
红色不仅限于红宝石湾这个名字……整座小岛上的百叶窗都涂成了红色。尤其是在圣—阿让市区。莫尔塞岛的红色相当出名,诺曼底的导游手册上对此大肆宣传。
这背后隐藏着什么?
青少年们又开始唱《克苇河的桥》。这首歌曾经是英国俘虏之歌。我却因为这首歌联想到这座小岛上的苦役犯监狱,也许我是唯一这样想的人。我们来到了十字路口,左侧是修道院的废墟,右侧是半岛荒地和我们的营地。远处正对的西北方就是马萨林监狱。
突然,队伍停下了哼唱。
远处监狱的栅栏处有一阵骚动。警车的鸣笛声、货车的嘟嘟声、人的尖叫声和狗吠声混杂在一起。通常来说,监狱那块儿总是一片静寂,偶尔看到几个神秘的警察或者游客出没。今天,远远就能看见警示灯在不停地闪。
整个团队激动不已。
“我们去看看?”马迪哈建议。
团员们一阵附和声。
悠悠犹豫了一下,其实他也想去的。但是斯蒂芬妮拦住了大家。
“年轻人就是这样,不行,回去!”
虽然大家也不情愿,但还是退缩了。监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阿尔芒耸了耸肩。
“不过是转移囚犯罢了。一个家伙到了,或者一个家伙出来。一天至少三次。如果你们只是因为两辆吉普车和三盏灯就激动不已……”
没人敢反驳他,特别是我。但我还是觉得他说的不对。平日里囚犯转移可不是这么大架势。今天发生的事情异乎寻常。但不关我事,我还有其他事情操心。
走进营地就没人唱歌了。无论如何,在杜瓦尔神父前打打闹闹就不太合适了。
“去洗澡吧,小滑头们。”悠悠吼道。
杜瓦尔神父从办公室走出来,那里之前是鸡舍,后来翻新做了办公室。他脸上挂着一副无法模仿的笑容从我们面前经过,很难判断是来关心我们还是准备训我们一顿。
杜瓦尔神父强调铁一般的纪律。他应该有70多岁了,是生物学家兼军事家。夏令营基地建在一个旧农场上,位于小岛人烟稀少的地方。古老的建筑物城墙,把我们像牲畜一样关在里面。自由活动只有一个小时,不多不少,活动范围也是规定好的,而且从不准单独行动。在帆船活动和集体活动之外,就不剩多少自由活动时间。总而言之,很难单独行动。
这一次,轮到斯蒂芬妮下命令了。
“埃米莉、尼科、奥德蕾,20分钟后来厨房!”
集体活动都是3人一组。准备饭菜、洗碗、收拾碗筷……6天轮换一次。因为我昨晚已经打过杂了,所以接下来的日子我没事。
运气不错。
我觉得这也是命运发出的信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