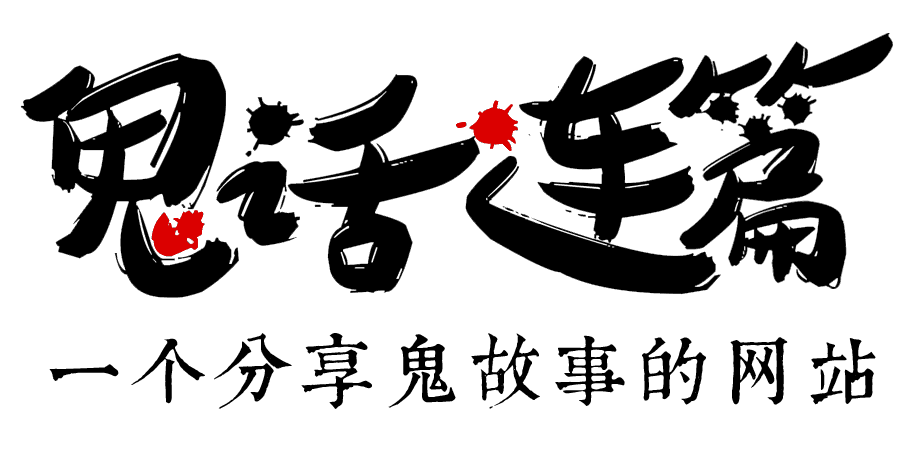一天傍晚,嫣语偎依在我身边,轻轻说道:“我知道你想什么,你彻底对这个世界失望了,可是你要记住,你至少还有我,即便是为了我,你也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一定……”泪水划过她的脸颊落在我的胸膛上,我像一株久旱的小草受到了雨露的滋润,重现出生机,我伸出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嫣语把我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是的,虽然整个宇宙都抛弃了我,但我的生命并非全无意义,我也并没有失去一切,我至少还有嫣语,为了她,我也要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
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尼雅就没有死。
活着,就是我们对命运最强的抗争。
时光流逝,转眼间六年过去了。
我们日复一日过着简单悠闲的日子,与千万年前的原始祖先不同的是,他们生活在生机勃勃的热带雨林中,而我们这个小部落却伴着宏伟却日渐残破的文明遗迹。
说起尼雅,她的变化是巨大的,当真是沧海桑田,山河剧变。曾经喧嚣的城市日渐残破,一些低矮的建筑物已经被黄土掩没,整个城市也被厚厚的灰尘笼罩,毫无生气地矗立在平原上,像一座怪石嶙峋的山脉。城外的黄土平原彻底变成了戈壁滩,并且正在迅速地沙漠化,纵横其间的道路早被掩埋,找不到一点痕迹了。
尼雅的气候也变幻莫测,一会儿还是晴空万里,转瞬间就说不定暴雨倾盆。城边的凌水河曾经是那样的美丽,如同一条银色的飘带轻柔地绕城而过,如今动不动就暴发洪水,河边的麦田被冲毁过好几次。幸好河边的温室还算坚固,里面的庄稼没有受到影响,以部落现有的人口,依靠温室内的收成就可以保证食用;室外种植的庄稼只不过是我们还在幻想着有一天其他地方的人类会迁移到这里来。
部落的人口稳定在一千五百人左右,当然,我们还是没有一个孩子出世,没有孩子的笑声和喧嚣,营地里显得是那么的冷清与落寞。
莫桑叔叔年纪大了,把族长的位置让给了我。其实当了族长也就是带着大家种植和收割庄稼,其他时间就只有坐在河边望着哗哗的河水发呆。
我总觉得不应该这样下去,我的心还没有死,也许尼雅上面还存在着一个没有被辐射污染的乐土,我们可以在那里繁衍生息;也许在尼雅的其他地方还有人活着,还掌握着文明。我总该去做些什么。
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嫣语。
“外面都是荒原,没有吃的也没有水,你能走多远呢?”她问。
“可以沿着凌水河走,能到达联峰山脉……”我说。
“那以后呢?”她追问。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回答。
沉默了一会儿,她说道:“你想去就去吧,但是无论你要去哪里,都必须带上我。
事也凑巧,后来我们在一座地下仓库里发现了大批武器和高密度超导电池。武器没什么用,但电池却可以让改装过的车子重新运转起来了,营地里甚至用上了久违的电灯。
有了车辆,我的想法无疑具有了非常高的可行性。于是在一天清晨,我和嫣语开着两辆装满补给的车子出发了。
我们沿着凌水河逆流而上,走了两天,来到了瑞卡姆城,这座旅游小城有著名的人类黑暗时期的城堡遗迹,如今现代与古代的建筑全被黄沙掩埋,没有一丝生气,没有一点人类曾经生存过的迹象。
再向前,平原已然变成浩瀚的大沙漠,我们一路前行,渐渐横穿了辽阔的拉卡拉大平原,不,现在应该叫做拉卡拉大沙漠了。其间,我们又经过了四座城市,遗憾的是没有遇到一个人,即使人类的白骨也早被黄沙掩埋了,视线所及,甚至找不到人类曾经存在的痕迹了。天气也十分糟糕,没有了植物的遮挡,沙漠里到处肆虐着猛烈的沙暴,我和嫣语几次险些葬身沙海。
我们终于来到了联峰山麓的拜丁,我曾经对这里抱有很大希望,它依山傍水,与庞嘉的地理环境非常相似,很可能有人幸存,但我们失望地发现,这座工业城市同样空无一人。
我们已经走了六百公里,在这个没有一点生命迹象的世界里独自行进这么远,没人能够形容我们心中的那份孤独。看得出嫣语早就想家了,但是她始终没有说出口,只是埋头默默跟随着我。
我一时彷徨了,难道整个尼雅就只有我们幸存下来了吗?不,我不相信!
我们翻越了联峰山脉继续旅行。
我们经过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丘陵之城阿桑达,彩虹之城霓彩,绿野明珠爱美兰……
我们一次次在荒芜人迹的废墟中徘徊,又一次次满怀希望向另一座城市出发……
终于有一天,我们来到了海滨城市卡来米亚,曾经的万帆之城。这里每年都要举行太阳帆船比赛,我和母亲曾经来过,那万帆竞渡的壮观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但现在,人们好像都乘坐帆船远航到世界的另一端去了,偌大一座城市空空如也,只有风在街头巷尾呜呜地掠过。
我和嫣语手拉手沿着海岸线默默走着,一边是波澜壮阔的大海,一边是沉寂的城市遗迹。
两行脚印一直伸向远方……
那是人类在尼雅最后的足迹吗?
清风拂过,脚印渐渐变浅,渐渐消失……
我把嫣语的手握得紧紧的,好像一不小心,她也会在风中消散,我几乎失去了所有同类,再不能没有她了。
我在一块礁石上坐了下来,眺望着茫茫的大海……
天慢慢暗下来,落日低垂在海天交界处,天边的云朵和海水被映衬得金光灿灿,但没过多久,随着落日沉去,一切都陷入黑暗。
太阳落下,明天还会照样升起,而人类呢?我所目睹的是不是尼雅最后的胜景?
我们回到了庞嘉,回到了我们那个小小的部落。全部的希望都泯灭了,我的心反而一片平和,每天只是带着族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又是五年过去了,平静的五年,身心渐渐老去的五年。
我本来以为我的一生就会这样过去了,看着族人们一个个死去,最后亲手埋葬自己的爱人,然后默默在蓝天与艳阳下停止呼吸,但是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开始它是微弱的,没有人注意到,但随着那声音逐渐强烈。我的心猛然一震,几乎遗忘的记忆重新涌上心头。我抬起头,向空中张望,果然,一架飞机出现在视野中。
刹那间,营地里一片沸腾,人们向着飞机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压抑已久的孤独和落寞一下子爆发为近乎疯狂的喜悦。
那是一架小型喷气式飞机,它在营地上空盘旋了两周,降落下来,一个飞行员走了出来。
我们像迎接天使一样把他拥进房间,端上我们自制的米酒和食物。对方忙不迭大吃起来,吃饱之后,他的表情却严肃起来,表示要单独与这里的族长谈谈。
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
“我叫米亚,谢谢你的款待,很久没有吃过新鲜的食物了。”对方说道。
“我是荆邢,你的到来让我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我回答。
“你一定期待着我带来其他人类的好消息。”米亚说。
我点点头,等待着他继续讲。人类的科技设备都被星潮摧毁了,米亚既然驾驶着飞机来到这里,就说明尼雅上还有一群人类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人类文明的火种还在。
“我的到来对你们来说肯定是今好消息。”米亚笑了笑,但是我注意到他的笑容有些僵硬,“的确,虽然我们走到了灭亡的边缘,但是还有一些人类幸存,我估计大约有三四万人吧,大家都分散在尼雅各地,被沙漠和大海所阻隔,成为一些与世隔绝的小群落,但是我想你我都清楚,尼雅文明已经毁灭,我们的未来毫无光明,即使我们所有人付出怎样的努力也无法挽回了。”米亚叹息一声,忧郁地望着我。
我沉默了一阵,问道:“我想,你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告诉我这些话吧。”
米亚没想到我这么问,笑道:“你的成熟和沉稳与你的年龄并不相符。”
“本来我的心已经死了,但是你的到来,为我带来了希望。”我说道。
我欣慰地看到米亚点了点头,但是他的表情仍旧严肃,“那可以说是一个希望。”他后来说的话开始让我感到震惊,“你看到了,我驾驶的飞机没有受到星潮的辐射,实际上我来自政府的一个秘密基地,这个基地早在星潮爆发前就建造好了,现在那里汇聚着尼雅最后的政治与科技精英,他们在制造最后一艘火种飞船,我曾经是那里的一名工程师。现在飞船即将建成,他们准备搭乘这艘飞船离去。”
“那我们呢?”我问。
米亚摇了摇头,“飞船的乘员有限,实际上,尼雅上还活着的人类全要被抛弃了,就因为这个,我才从那里逃出来。自己要可耻地逃走,却留下众多同类无助地走向死亡,我的良知无法容忍这么贪婪的行为,所以我要联系还活着的人们去反对他们。”沉默,我被他的话惊住了,一时间被欺骗和抛弃的感觉化为一团不可抑制的怒火燃烧起来,“需要我们做什么?”我问道。
“我需要战士!”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带着你的族人,拿着能找到的武器,到那里去,要么我们一同离开,要么就共同毁灭!”
米亚匆匆地走了,他还要去联络其他地方的人类。
三天后我们也出发了。
我原本只想带走强壮的男子,但是没有人愿意留下,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更不在乎失去生命,我们都是不怕死的战士。
长长的车队带着食物和饮用水,带着大量武器和能量电池,带着心中的一丝希望,向沙漠中行去……
我们的目标是八千公里外的千壑山脉,生存与灭亡,希望与泯灭,都将在那里走向最后的终结!
火种
我们风餐露宿,日夜兼程。
一路上仍旧没有见到一个人。
我心头甚至出现一丝疑虑,米亚真的来过吗?千壑山脉的事情是真的吗?还是我们因为极度孤独而集体产生的幻觉?
极目眺望,人类的遗迹也看不到了,岁月的刻刀真是锋利啊,才短短二十年光景,尼雅大地又重归蛮荒。
不断有人倒下,魂归尼雅的历史长卷,活着的人都变得无动于衷,大家的心中只有一个意念——走下去才有希望。
终于有一天,一道青色的山脉横亘在眼前,几道浓重的烟柱正从山脉深处腾起。
翻过山峰,穿过峡谷,人类最后的基地展现在眼前。它像是十几个半球状的坟丘散落在群山环绕的谷地中,看上去并不起眼,但我们都清楚,上面的结构不过是抵御星潮的保护层,真正的主体一定深埋在地下,不知会有多么宏大。
基地附近一片令人热血沸腾的景象,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彻山谷,许多人影在硝烟与火焰中晃动。
一定是率先到达的部落与基地发生了交火,不过看起来基地的卫戍部队占了上风,许多衣衫褴褛的部民正纷纷后撤,不时有人中弹倒下,在他们身后,身穿军装的政府士兵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正有条不紊地压上来。
我们的车队不经意间贸然闯入了战场。族人们有些惊慌失措,纷纷把目光投向我。大家曾经是工程师、工人和政府公务员,后来成了彻底的农民,但是没有人当过军人,更没人经历过这样的战争场面。
一个身材高大但蓬头垢面的男子冲到我面前喊道:“新来的?”
我点点头。
“还不快上?要是顶不住,大家就都完啦。”对方布满血丝的眼睛迸射着疯狂的光芒。
我二话不说,带着人冲了上去。
没有战术动作。没有进攻队形,大家一窝蜂似的拥了上去,有的人盲目射击,有的人捂着头趴在地上瑟瑟发抖,我们根本是一群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好在政府军见我们人数众多,又摸不清底细,暂时退了回去。
枪声稀疏下来,战斗双方终于脱离了接触。
我们与其他部族会合,这么些年见不到自己的同类,如今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大家本应喜极相泣,但现在人们都紧绷着脸,默默埋葬着死去的同伴。
率先到达的一共有从三个城市来的部族,总计两千余人,已经对基地发动了三次进攻。基地内的部队人数并不多,大约只有一千人,但是武器精良、训练有素。这几仗下来,部族一方折损近半,剩下的人也都情绪低落。我们的到来一方面再次建立起数量优势,一方面重新鼓舞起大家的信心。
过了四天,米亚驾驶飞机回来了,过了一个多月,又有四个部族赶来,这下我们大约有六千人了,于是几天后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经过连续几次战斗,基地方面明显不敌,纷纷退入地下,我们占领了所有地表建筑。
正在连夜商讨进攻方案的时候,基地方面却派来了谈判代表,他们提出,大家是尼雅仅存的人类,不要再互相残杀了,要求我们先退回原来的营地,然后大家坐下来就未来的命运好好商谈。
我们经过会议后,同意了对方的意见。
部族的队伍离开基地入口,向营地撤去。基地部队开始回到地面,在原来的阵地布防。但是他们没有察觉,在一栋废弃的建筑内,我和另一个部落首领带着四百人悄悄潜伏着,在我们三十米外是一个偏僻的通风口,上面已经布设了炸药,从那里我们可以一直深入地下城。
一辆装甲车从基地中驶出,向部族的营地开去,大概是派来谈判的,基地的部队还在忙着调动,根本没人发现我们。
一声爆炸骤然响起,通风口被炸了一个大洞,我一跃而起,带着大家冲了出去。我进入通风口的时候,看到基地部队正试图向我们发动进攻,但是又被从营地杀回的部族部队纠缠住。整个地表顿时杀声骤起。
通过倾斜的通风口,我们来到一条宽阔的隧道。地面的枪声一下子变得微弱,几不可闻。隧道内空无一人,一片寂静,看来基地的部队都被调到了地面。
除了几个人原地留守,阻击尾随的敌人,我们向基地深处跑去。
隧道在昏黄的灯光映衬下,一直伸向黑暗中,仿佛永远也没有尽头。我忽然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记得在星潮爆发前后的几年间,自己就是在地下城中度过的,这迷宫样的隧道,这昏暗幽深的气氛是那么的熟悉,仿佛还残留着我和伙伴们嬉戏的身影,现在我们却要在这里与自己的同类生死相搏,甚至同归于尽。
前进了几百米,我们开始遭到抵抗,但是对方的人数不多,又是仓促迎战,很快被我们肃清。我们继续向基地纵深发展,但让人头疼的是基地中复杂的隧道系统四通八达,蛛网一般,连米亚也弄不清楚,我们一路上只得不断分兵探索。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已经进入基地深处。此刻基地中到处是爆炸声和人们疯狂的嘶喊声,双方的士兵混杂在一起,乱作一团。
我身边只有二十多人了,遇到的抵抗越来越顽强,对方宁死也不后退半步,不过这也使我明白,我们现在非常接近基地的核心了。对方倒下的人员都身着便装或者白色工作服,而没有了正规军人,这更加印证了我的看法。
再加一把劲,敌人就会彻底崩溃!
前面又一道防护门拦住去路,我们正布置炸药试图将其炸开,门忽然自动打开了,门后出现一片敌人,双方骤然零距离遭遇,顿时展开一阵乱战。
灼热的能量光束在人群中交织成密集的死亡之网,士兵们像收割的麦子一般一片片倒下,冲撞在一起的人们互相纠缠着,厮打着,刺刀和匕首闪着银光溅起一道道血花。
周围终于陷入沉寂,我踉跄着爬起来,目之所及到处是烧得焦炭一样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焦煳味,我禁不住剧烈呕吐起来。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星潮的咆哮已经让人类陷入绝境,为什么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共渡难关,反而要为了一己私利而自相残杀?
一股不可抑制的怒火在我心头腾起,说什么黑洞、星潮、辐射、饥荒,人心才是最险恶与危险的,就让人类在最后的疯狂中走向毁灭吧!
我重新端起枪,一个人向里面冲去。
奇怪的是,一路上没有再碰到一个人。我一个人狂奔在空旷的隧道中显得有些可笑。
一个拱形的洞口出现了,我冲了进去,里面是一个半球形大厅,简直和我记忆中观看星潮来临的大厅如出一辙。大厅内坐着十几个人,他们见到我并没有表现出惊慌,反而很平静的样子,这更加激怒了我,我毫不留情地扣下扳机,死光无情地扫过大厅,把掠过的一切都彻底烧焦。
从大厅出来,我继续向前跑,我的脑海中早忘了什么飞船,逃生的概念,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杀,杀死遇到的每一个人。
我又冲进一座建筑,这是一个很小的房间,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坐在椅子上望着我。我没有犹豫,立刻开枪,死光将桌子熔为两半,击中了老人的腹部。我回身正准备离开,老人忽然说了两个字,我刹那间愣在当地。虽然老人的声音有些模糊,但我能听清,他在唤着我的名字“荆邢”。
我回头凝视着老人,我一下子认出来了,那正是我失散多年的父亲。天哪,我竟然杀了自己的父亲!仿佛有一道闪电击中了我,疯狂与杀戮都烟消云散,我的脑海中重新浮现出童年的景象:父亲把我举过头顶,让我俯瞰着尼雅美丽的平原、山脉和城市……父亲出现在火种飞船离去的背景中,张开他的双臂把我和母亲拥在怀中……父亲和我望着生命绝迹的尼雅,他伸出手轻轻抚着我的头……
我扔下了枪,一头扑进父亲怀中。
“是你吗?我亲爱的孩子,我是在做梦吗?”父亲喃喃说道。
我抬起头端详着父亲的脸庞,泪水已经布满我的脸颊,“爸爸,是我呀,你怎么会在这里,我和妈妈都以为你死了。你为什么要抛下我和妈妈?为什么呀?”
“唉,乱世啊!”父亲叹息一声,他展开左手,母亲的那枚钻石戒指出现在他掌心,“从地下城秘密通道撤出后,我到庞嘉城找过你们几次,直到我在一个死去的暴徒身上找到了这枚戒指,很难有人在辐射中生存,所以我以为你们早就……”父亲的声音哽咽着,“这些年我天天都在想念着你们,当真度日如年,如果不是为了飞船,我早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妈妈临死前一直在念着你的名字,这……这个残酷的世界啊……”我抚摸着父亲焦黑的伤口,绝望地吼道,“不,我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我不能让你死……”
父亲像小时候那样轻轻抚摸着我的头,“好啦,能够见到你,已经是命运对我的眷顾啦,我很高兴去和你的母亲相聚。”
“都是那该死的飞船,人类的最后一点良知都因它而泯灭。”我抹去泪水,抓起了枪,“我这就去毁了它,谁也别想离开,大家都来为尼雅殉葬吧。”
“冷静一些,陪爸爸坐一会儿吧。”父亲苦笑着对我招招手,“那最后一艘火种飞船根本不是用来移民的,它的体积太小了,没有人能乘着它离开。”父亲发出了一声呻吟,我连忙抱住他。
父亲和蔼地望着我,笑了笑说道:“当年我没有离开尼雅,一方面是舍不得你和你母亲,另一个原因就是‘火种计划’。由于时间紧迫,移民工程进行得非常仓促,直到最后阶段才发现移民的目的地,桃源星系三号星,与当初观测的环境差异非常巨大,人类根本无法在那里生存下去,但那时候一切都已来不及更改,我们只能坚持着把移民计划进行完。但愿离去的那些人类在抵达那里后能够找到新的办法,但机会实在极为渺茫。”父亲长长叹了一口气,“大部分科学界精英都留了下来,尝试着能否找到新的办法让人类生存下去。”
“所以在地下城的时候,你们仍然在夜以继日地研究?”我问道。
父亲点了点头道:“我们原本怀疑星潮的破坏性,期望星潮过后人类还能够继续在尼雅生存下去,但现实无情地击碎了我们的幻想,当然我们没想到人类社会竟然那么快陷入崩溃,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啊!”父亲的眼中闪烁着泪光,他一定在回忆着地下城中的暴乱,回忆着一座座哀鸿遍地的城市遗迹……
“迁徙到这个基地之后,我们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宇宙深处。”父亲继续说道,“经过对大量资料的重新汇总,我们失望地发现,在三千光年的范围内根本找不到一颗可以供生命繁衍的行星,而以我们的宇航能力即使一千光年也无法越过,这说明通往群星的大门对我们紧紧关闭着,人类只有和尼雅一同走向灭亡。那些日子里,基地被绝望的气氛所笼罩,好在经历了一连串的灾难,我们已经能够冷静下来,坦然面对现实了,我们再次投入近乎疯狂的工作之中。我的研究领域是宇航推进技术,最初制造的飞船动力系统太庞大了,效率也过于低下,严重限制了远距离的宇宙航行。我发现星潮倒不全是坏处,它所喷射出的高能粒子潮恰恰可以成为飞船的动力,就像大海上的风,能够把星际飞船加速到光速的80%,一直吹向遥远的宇宙深空,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发现,但是无疑对我们的宇航具有重要意义。”父亲的脸上显出自豪的光彩,但是我感到他的呼吸正在微弱下去,“我们还在五千光年外发现了一颗行星,那里已经有了原始生物活动的迹象,于是我们开始制造最后一艘火种飞船。我们的资源已经不能建造大型飞船了,这艘飞船很小,连一个人也坐不下,但是它的意义是此前的所有火种飞船无法比拟的。尼雅人类的毁灭已不可避免,作为文明,我们会在宇宙中彻底消失,但是我们将在宇宙深处埋下一颗种子,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获得新生。”父亲向我投来欣慰的目光。
“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们呢?”我痛苦地问道。
“我们解释过,可谁会相信呢?”父亲惨然一笑,“为了一线虚无缥缈的生机,人类的理智早被贪婪与自私淹没了。好啦,爸爸很困,我想睡啦。”
“不,不,醒一醒,你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我拼命摇晃着父亲的身体。
这时,大地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抱着父亲摔倒在地,接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骤然响起,又逐渐远去。
“飞船发射啦。”父亲的眼中突然迸射出异样的光彩,然后又暗淡下去,直至失去光泽。
我抱着父亲的尸体,纵声大哭,但是我的哭声很快就被连续不断的枪声和爆炸声淹没了。
新生
尼雅默默悬浮在冰冷孤寂的宇宙之海。她曾是罕有的生命与文明的摇篮,但是现在,沙漠像瘟疫一般布满了曾经生机勃勃的绿色大陆,全球范围漂浮的沙尘暴使她的星光变得那么暗淡。一艘小小的飞船拖着长长的尾焰冲天而起,瞬间没入漆黑的宇宙……它就像生命最后的一缕魂魄从尼雅上消散。
不,其实它也是一颗文明的火种,带着尼雅人类最后的希望,去找寻生命的另一个家园。可是它的体积是那么小,怎么能跨越那么漫长的时间与空间的旅程呢?况且它的航向也不对,它怎么正在向着阿特拉斯星核飞去呢?那里可是生命的禁区呀,正在猛烈喷发的星潮更会让它粉身碎骨,可这艘渺小的飞船仍像是投火的飞蛾,执著地向着咆哮的星潮挺进……
飞船已经进入星潮的滔天巨浪之中,还在向着星潮高密度粒子区域前进。飞船的头部是一个盾形防御结构,可以暂时抵御星潮的冲击,但是在这个高能量冲击的环境中,它坚持不了多久。
突然间,那占据了飞船三分之一的盾形结构迎着星潮伸展开来,成为一把圆形的大伞,一道无形的薄膜从伞的边缘向四周伸展开去,那薄膜是无法察觉的,但是星潮粒子在薄膜上面反射出夺目的光彩。
薄膜不断伸展着,满满的,半径竟达两千公里,像是星潮中飘扬而起的一面巨帆。
终于,飞船在星潮中汲取了足够的能量,接着,它调转了航向,像是黑暗中破茧而出的蝴蝶,舒展着华丽的翅膀,向着更深的宇宙飞去……
一万年后。
这颗蓝色的星球还是宇宙的新生儿。
在高耸的雪山脚下,在灰暗阴冷的森林深处,一只雄性原生猿正在拼命奔跑,在他的身后,两只凶猛的树熊已经越来越近了。
他知道自己终究无法逃脱,他只想把它们引得越远越好,他的同伴们正躲在附近的一个树洞中瑟瑟发抖。
终于,他感到一阵撕裂般的剧痛,随即摔倒在地。
他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他的生命在一秒钟之后就会消逝,他的目光掠过树熊张开的血盆大口,望见了一抹湛蓝的天空。
这个时候,一团火球划过天空,接着整个天空仿佛都被点燃了,然后一股猛烈的气浪把他连同树熊一起掀上了半空。
他苏醒之后,发现自己还活着,这简直是个奇迹。半个森林都不见了,变成了一个一片狼藉的巨坑,而另一半森林正在熊熊燃烧。
他茫然站立在大坑的边缘,几个幸存的同伴默默走到他身边。
在巨坑的中心,一个黑乎乎的物体悄无声息地展开,一股无法察觉的微生物像雾一样消散在空气中。
几天之后,一场致命的瘟疫开始在全球范围蔓延,数不清的树木枯萎了,数不清的动物哀鸣着死去。
这是一次毁灭性的瘟疫,最终有百分之九十的动植物死去了。
多年以后,原生猿的首领带着他的部族向草原迁徙。在这次灾难中,虽然部族的损失同样惨重,但是他和其他几个同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而且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一些他自己也无法察觉的变化。
在他的基因序列里已然刻下了另一种生物的特殊序列!
死亡,在某种时候,也意味着另一次新生!
八千万年后。
这是个美丽的夜晚,繁星在夜空中闪闪烁烁,大海在星光下微微涌动。
父亲和母亲领着小孩在海滩上散步。
“你们说,我是从哪里来的呢?”男孩忽然问。
“你是爸爸和妈妈相爱之后生下来的呀。”母亲回答。
“那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呢?”男孩很认真地问。
母亲被孩子这个复杂的问题问得啼笑皆非。
男孩指着一天繁星说道:“我知道了,你们一定是从很远的星星上来的。”
父亲的心悠然一动,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人类身体内的一小段神秘的基因序列并不存在于其他生物体内,男孩天真的话或许正道破了文明中最大的一个谜题。
父亲轻抚着男孩的肩膀,和他一起仰望着满天星辰,缓缓说道:“也许吧,也许我们就来自哪一颗遥远的星星上。”
⊙文学短评
有关星潮的恐惧和文明重建的努力,在苏学军的《末日火种》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地下城中的暴乱,一座座哀鸿遍地的城市遗迹,以及“我”失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尼雅人类也不可避免地毁灭。在毁灭性的劫难之中,文明濒临崩溃,人类的理性也为暴力所取代。这些都是末日想象中常见的主题。就像《2012》中的“诺亚方舟”保留着人类火种一样,小说最后,一颗文明的火种,带着尼雅人类最后的希望,去找寻生命的另一个家园,这终究给了人们些许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