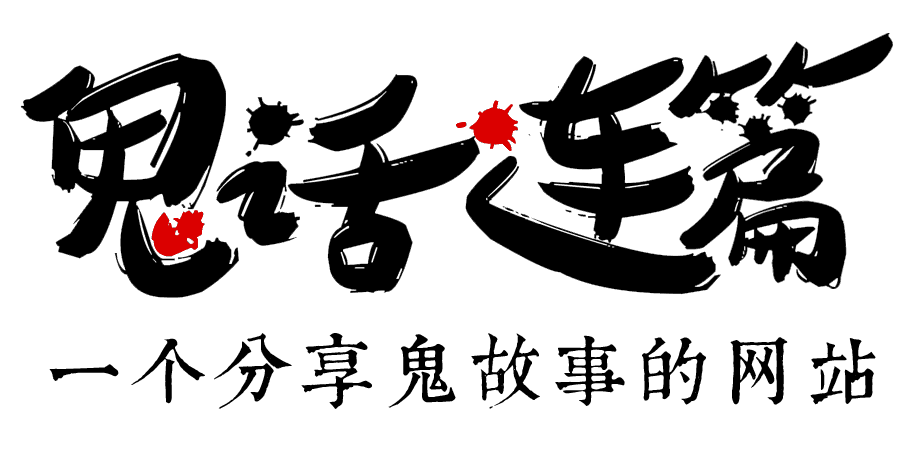顾问骞到的时候,红日门口只有一辆宾利,徐奔先到了,派出所的片警还没到。他下了车就往红日疾冲,还是从白色的门进的。司罕紧追其后,但有点跟不上他的脚步,还是从红色的门进的。
一点没犹豫,顾问骞直奔通往地下室的黑门,到那儿时,果然发现门上的钥匙锁断了,电子锁开着。他拉开门正要下去,被司罕喊住了。司罕大步跑上来,先顾问骞一步下了阶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粉色的迷你手电筒,打开,照亮底下那个漆黑、不见底的楼梯。
“你不是怕黑,我走前面。”司罕喘着气,回头道。
顾问骞愣了一下,从追车以来一直严肃的面容出现了片刻迟钝,他甚至反应了一会儿。他不过是在坦白局上随口说了一句,自己都忘了,这人居然记得。照这人的性子,记得也该是为了调侃,可司罕的神情又很寻常,好像真的只是记起了一件需要注意的事而已。
顾问骞沉默了一会儿,上前拿走了司罕手里的粉色手电筒,走在了他前面。“早就不怕了。”
楼梯很长,顾问骞拔了颗纽扣扔下去,听了听声音,大概有十几米深。迷你手电筒聚光功能再优越,也不是战术照明灯,只能看清两米内的情况,他始终走在司罕前面一米。
下到楼梯的尽头,是一扇门,只有很厚的门框,没有门板,配有设备,司罕立马认出来:“雾化消毒门。”
顾问骞让司罕退后,他掩着口鼻先进去,确认是常规的智能雾化消毒门,司罕才跟着进去。他们迈了两步就停了,眼前又是一扇门,这次是无菌门,已经被拉开了一小半,显然有人刚进去了。
司罕咕哝道:“里面难道是个无菌室?”
两人迈进去后,司罕的话卡住了,他一瞬间都觉得自己走反了,沿楼梯往上走才是“进入”。
这是一个空旷的场所。司罕原本以为黑门下面是个地下室、密室之类的,但他天真了,这不是密室,这是个地下广场,漆黑,庞大,让人眼花缭乱。这个地下广场的面积可能有十几个红日那么大,摆放着许多器械,有超低温冰箱、液氮罐、移液器、离心机、PCR仪……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器械,东边的墙上是一大片超级计算机,占满整个墙壁,这是何等夸张的设备。地上的器械摆放非常凌乱,像是刚被洗劫过,所有器械都已经停工了,整个场所的电闸是拉掉的,没开灯,非常暗。
他们之所以能看清这里的情况,是靠分布在这个地下广场的几十个玻璃培养缸。这些培养缸里亮着颜色不同的灯,装着许多生物标本和器官,液体还在运动。电源好像是自供的,培养缸的大小各异,最大的缸有两个人那么高,里面是一只泡涨了的羊——他们姑且把它当成羊,最小的只能称作培养皿,只有巴掌大,里面是一些菌群。
这些培养缸分别打着红色和白色的光,在漆黑一片的地下广场里,像是一簇簇鬼火。培养缸里的生物标本,像在鬼火中灼烧,仿佛是这些死去的、残破的器官在照亮整个空间,看起来分外阴森。
顾问骞警惕地朝前走了起来,脚步逐渐加快,这里太大了,司罕紧跟着,路上踢到了几袋酵母,粉末沾到了衣角上。培养缸的红光和白光不时扫过疾走中的两人的脸,亮一下,没入黑暗,亮一下,没入黑暗。
两人开始越走越快,这里的氛围太压抑了,红光,白光,黑底,这三个配色让人不由得和上面的红日联系起来,这里就像个更大更原始的红日,拥有同样错综复杂的通路。
那个名叫红日的女孩,就生活在这样庞大的地下广场。她经过每个地方时,是不是都能感受到头上传来的活人的气息?那首《红日》能不能传到这幽深的地底?
司罕甚至一边跑一边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地下广场的电闸拉了,为什么这些培养缸的灯亮着?是亮给他们看的。为什么要亮给他们看?就像红日里那些红白黑的门,是造给人看的,是徐奔要给他们看的。
红白黑,是徐奔所有的情绪。红色的愤怒、黑色的恐惧、白色的哀伤,他拥有这么多负面情绪,唯独没有快乐。红日的每一条曲折如沟壑的通道,都是他内心的深渊,是他循环的痛苦。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日常生活的地方建造成这样?红日就是徐奔的象征,他们此刻仿佛永远都跑不完的地下广场,就是徐奔的精神世界。
走了好一会儿,顾问骞突然停了下来,司罕跟着停下,问他怎么了。顾问骞站定脚,往头顶看。“这个位置,是废弃游乐场的大门。”
顾不上诧异他精准得离谱的方向感,司罕一顿,回头看,他们已经跑出了好远,红日仅仅是废弃游乐场的一个鬼屋,而这个地下广场的空间,竟有一个游乐场那么大,红日渺小得仿佛只是一个通往地下广场的入口。
司罕蹙眉,脑中忽然一闪而过了什么,他看着四周的摆设道:“这是个大型的生物实验室。”
顾问骞立刻打电话给姜河:“你查一下,当初买下废弃游乐场这片地的人是谁,是不是徐奔。”
他们显然想到了同一件事。徐奔曾说过红日成立的历史,废弃游乐场本是被一个买家买下的,要造一个生物工程的工厂,但被周边的居民以环境噪声污染为由联名抵制,国土资源局便一直没批下项目用地预审书,工厂没造成,两边在拉锯,徐奔就趁着双方拉锯期,把红日这个游乐场鬼屋利用起来,办互助组。
但现在的场面说明一件事,这个工厂可能还是建造了,不在明面上,而是避开政府和居民的目光,以红日这个不起眼的公益场所做掩护,在它的地下开发,买家从一个大型工厂的老板,摇身一变,成了公益互助中心的组织者,红日只是这个地下工厂的入口。
如果这是真的,那也说通了,六年前市三院车祸一事其实影响没那么大,徐奔这个院长却主动从市三院引咎离职,来这里做互助中心,不是出于愧疚,他就是开拓了新业务,来运营工厂的。
两人一时都没说话,疾走导致的喘息声在过分安静的地下格外明显。他们的呼吸起伏,似乎与培养缸里液体的运动有种呼应。如果这是真的,那红日的几十个患者,都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为这个地下非法工厂打了掩护。
姜河的电话回得很快,接起来就听到三个字:“是徐奔。”
猜测被印证了,两人都蹙起眉,气氛更凝重了。顾问骞朝四处望去,寻找徐奔的身影,但一无所获。他脱逃回到这大本营,是想做什么?
突然,空旷的地下广场响起一声刺耳的电磁干扰声,是从广播里传出的,许多个广播形成了环绕音,让人头皮发麻。紧接着是一声轰鸣,司罕没防备,双手紧紧捂住耳朵,依然觉得耳内刺痛,差点没站稳,是顾问骞扶住他的。
声音只持续了几秒就消失了,司罕有些眩晕,出现了耳鸣,听力都下降了。顾问骞的声音逐渐从模糊变得清晰。
“是震爆弹。”顾问骞面色凝重。这是一种非致命性警用武器,用巨大的声音让人短暂失去听力,从而失去行动力,用来震慑歹徒和控制人群骚乱。
司罕忍着眩晕导致的恶心,还有精力调侃一句:“我现在知道‘吃鸡’指《和平精英》或《绝地求生》等战术竞技型射击类沙盒游戏。——编者注的震爆弹只是游戏级别了。”
顾问骞道:“这也不是真的震爆弹,是录音,这是录下来的震爆弹的声音,威力不足真的震爆弹的三成,不然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听到我说话?”
“录音?”
顾问骞看向广场四周,光线很差,他并不能确定具体的广播位置,里面传出的环绕音还在继续,窸窸窣窣的,现在好像是几个人在跑步的动静,还有喘息声。
司罕也明白过来,地下广场的所有广播正在放一段录音,刚刚的震爆弹,是录音中的一个片段。
徐奔放的?他为什么要放?这是什么录音?
姜河的电话打了进来。刚刚因为震爆弹,忙乱中电话被挂掉了。
“怎么回事,震爆弹?”接起来就是姜河严肃的问话。
“人没事,是录音。”
姜河还想再说什么,广播里却突然传出了人声,似乎是几个人在疾跑中大喊。
“现在怎么办,跳不跳?前面就到底了。”
这是一个断续的青年男声,是喊出来的,似乎是被之前的震爆弹影响了,要扯着嗓子喊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司罕没来得及意会,在听到这句话时,他看到顾问骞的脸瞬间煞白,表情是难以置信的。
广播里依然是持续的喘息和跑动声,跑动声中有鞋子踏在钢板上的动静,还有一些风声,混着哗哗的摇曳声。司罕也是听了会儿才听出来,那个哗哗的摇曳声,是水声,庞大的水声,起伏跌宕,但有规律,和风一起……广播里的录音是在海上录的?
“我……我怎么听到了老东的声音?”姜河在电话里道。向来讲话凌厉不客气的姜河,问出这话时却有不易察觉的颤抖。
没有人回应他,顾问骞僵直得像具尸体。
广播里传出了又一个人声,是另一个男性,他急促地喊了一句:“顾队!跳不跳?”
几秒后,一个沉稳而熟悉的声音响起:“跳!”
扑通几下先后入水的声音格外清晰,摇曳的海声更大了,录音设备在水中发出嗡鸣声,非常混乱,一会儿是水下的宁静,一会儿是出水后人声、水声和扑腾声的交杂。逐渐听不清里面的人在讲什么了,落水后的人好似陷入了某种巨大的恐慌,有什么东西过来了,紧接着是第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惨叫很快没了,人似是被拖到了水中,只剩剧烈起伏的水的动静,那极其短促的一声惨叫,让人只凭声音便在脑海中勾勒出了一幅难以言喻的恐怖画面。
短促的惨叫声又接连响起了三次,来自不同的人,而后是两声枪响。那枪声不慌不忙,好似在等着什么,有种戏弄的味道。而在那枪响之前,司罕捕捉到了混乱中,被水声掩盖的一声咆哮。司罕从来不知道这个人还能发出这样悲痛欲绝的声音,他在喊“东子”,喊声稍纵即逝,被水声淹没了。
太混乱了,只是听着,司罕都觉得头痛,刚才震爆弹的威力似乎延迟到这一刻才开始发作。司罕的头很痛,他甚至有点不敢去看顾问骞此时的表情,好像不看,就不存在一样。这个人正在被凌迟啊。
这段录音,是顾问骞既往的经历。应该是那种,只是轻轻点一下,都能将他挫骨扬灰的经历。
姜河也没再出过声。
广播里的录音结束于最后那两声枪响。昏暗的地下广场恢复了静谧,这静谧却仿佛有回音,越是静谧,刚才兵荒马乱的声音后效越是绵长,这份静谧都变得尖锐嘈杂起来。很快,广播里又传出一阵电磁干扰声,而后是一阵令人耳鸣的巨响,接着是跑动喘息的人声。
重播了。司罕愕然。广播重播了刚才那段录音,一遍又一遍。这摆明了是在折磨顾问骞。
顾问骞终于从僵直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双眼骤然赤红,面目变得极其可怖,司罕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气息收敛了,状态如鹰隼一般,环顾着四周,蓄势待发,他好像能嗅到猎物就在近处一样。
司罕也跟着环顾了起来,既然放录音是为了折磨顾问骞,那这个人必然正躲在近处,仔细欣赏着顾问骞最细微的痛苦反应。
这是他们下来后,离徐奔最近的一刻。
但这里光线太暗了,颜色鲜亮的培养缸把视野弄得混乱,司罕和先前一样什么都没找到。不过顾问骞的动态视力和他差别甚大,果然,几秒后,那人的目光停住了,盯着西南方向昏暗漆黑的空旷处。司罕顺着这目光看过去,果然在阴影中看到了一个人的轮廓,是徐奔。
徐奔发现自己被看到了,也不躲,似乎在气定神闲地等着,挑衅一般,配合着广播里传出的一句句对话和惨叫,对顾问骞形成一种扑面的嘲讽和鞭笞。
顾问骞身体前倾,已经要冲过去了,司罕能感受到他怒极,这个人好像越是愤怒,越是冷静。但这种冷静就像核裂变。司罕第一次学到链式反应时,就觉得它有种失控的冷静,每个原子核的裂变引起另外好几个原子核的裂变,有条不紊地失控着,爆发的能量却是恐怖的。像踩油门的顾问骞,像此刻的顾问骞。
但顾问骞没有如他预料的那般朝徐奔弹射出去,而是转过了身,一把抓住司罕,把他塞到了最近的桌子底下。
“不要出来。”话语认真,有种威胁的意味,好像司罕要是敢出去,会先死在他手上。
广播里又进行到了“跳不跳”,那样危急的关头,那个“跳”字,依然说得冷静,掷地有声,和这四个字一样。
顾问骞把手机扔给了司罕,还在通话中,对面是姜河。
“两分钟内,必须赶到。”话是对姜河说的,声音有些沙哑。司罕又听出了威胁之意,好像两分钟内姜河不赶到,就不要怪他做出什么无法收拾的事来。
交代完,顾问骞朝着徐奔走去了,越走越快,直至跑了起来。
司罕对着手机问:“你们到哪儿了?他现在一个人过去找徐奔了。”
姜河这次一反常态地没有劝顾问骞什么,甚至没有跳脚,只对司罕严肃道:“你别管他,你躲好,我们已经到游乐场门口了,在我们下来之前你都别动。”
电话里传出了开车门声和训练有素的脚步声。如果顾问骞对所在位置判断得没错,那他们此刻就在司罕这个位置的头顶地面上。
“我要去拦住他吗?”司罕问。
“说了你别管。”姜河的声音有点暴躁,“你老实待着。”
“徐奔有枪。”
司罕从此刻躲着的位置,能清楚看到,徐奔在顾问骞朝他走去的时候,就拿出了枪,摆弄了一下,似乎在明晃晃地勾引顾问骞主动去送死。顾问骞非但没停,还更快地朝他直直奔去,跟疯子一样,用肉身嘲讽他的枪口。
姜河只顿了一瞬,咬牙切齿道:“那你就更不能出去。”
姜河调整了语气,听得出是在疾跑,声音认真而严厉:“司罕,你听着,你不可以在这里出事,你哪怕出来了死在任何地方,都不可以是在这里,不可以是在顾问骞的面前,现在能毁掉他的不是枪,是你,懂吗?”姜河的话,配合着广播里那几人撕心裂肺的惨叫,愈加振聋发聩。
他怎么会不懂。
身为一个警务人员,姜河这话已经偏离正轨了,但此时他也顾不上了。司罕这个人他就没看透过,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刺激到这个浑不论的,只能尽可能直白。
没得到回答,姜河急道:“你相信我,他不会出事,徐奔不是专业的枪手,奈何不了他,他的外号叫顾一百。”
“顾一百?”
姜河一边向身后的警务队用手势布局,一边转移着司罕的注意力,让他别轻举妄动:“听过二十一英尺(约六点四米)法则吗?”
二十一英尺法则,是警务训练中对人的反应区间的总结。一个健康的成年男性,可以在一点五秒内迅速移动至二十一英尺远的地方,这一点五秒,是一个严格受训的警员,用手枪准确击中一个人的反应时间。如果持刀歹徒与持枪警察的距离小于二十一英尺,持枪警察不能保证在被歹徒刺伤之前,完成拔枪、上膛等动作。在二十一英尺以内,刀比枪有效,一个训练有素的刀客,可以在这个距离内快速消灭一个持枪者。
早年就有专家提出,二十一英尺的距离也不足以保证安全,距离达到五十英尺(约十五米)甚至一百英尺(约三十米),也不能保证不被持刀者杀伤,这就是为什么持短兵者有时能压制持枪者。反过来,如果持枪的是歹徒,面对持刀的警察,歹徒未必受过良好的枪械训练,警察的机会更大。
顾问骞就是践行这项法则的佼佼者。他在武警学校时就是冷兵器爱好者,训练时的最高纪录是在一百英尺的初始距离下,单刀缴械持枪的警员。
姜河始终记得那年刚入学的自己,看到顾问骞那场实战演习,像见了神,差点没自闭退学。顾问骞第一次出手就打破了警校的传奇纪录,那个纪录,据说是几十年前一个得天独厚的特种兵留下的,那人当时就被称为突破人体极限的奇迹,顾问骞随手就破掉了这个纪录,他那时就思忖,这个突然转来的学长,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顾问骞不是和大家一样考入学的,他是某天被送进来的,进来就是高年级,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头,谣言和编派不断,但饱受质疑排挤的转学生,用那场实战让所有人闭了嘴。
姜河至今都觉得,顾问骞被大家送外号顾一百,只是因为实战规定的最长距离只有一百英尺,再加距离,他或许也能办到。
司罕看到顾问骞似乎印证着姜河的话,在徐奔开枪前,几个疾跑和跳跃,居然就从三十米开外冲到徐奔面前了。徐奔只来得及开了两枪,那两枪和广播里的枪声呼应上了,但顾问骞的移动速度太快,那两枪看着甚至像是故意打偏的,枪口来不及瞄准移动中的顾问骞,人也来不及警戒。
徐奔很快意识到,在这个距离下,枪对顾问骞没用,而对方手里那把在培养缸的光下一闪而过的蜘蛛折刀,已经晃到他的眼睛了。徐奔很果断地收了枪,朝地上一滚,以一个格斗姿势制造攻击方向的偏移,留出反应时间,避开从正前方来的袭击,然后借着后滚的动势逃跑。
斜后方有一扇不显眼的白色小门,他钻了进去,用门墙阻隔了顾问骞凶猛的追击。顾问骞反应很快,没有被奔跑的惯性牵绊,瞬间转换了方向,也追进了斜后方的小门,两人消失在司罕的视野中。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空旷的地下广场只剩下广播里的动静,枪响过后,熟悉的轰鸣声响起,录音又开始从头播放。
司罕从桌下钻了出来。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桌子移动的声音,姜河立刻急道:“你在干什么!你待着别出去!”
“我给你留了记号。”
姜河心肝脾肺都要炸了:“你别去给他添乱!他不会有事!”
“我不是担心他,我是担心徐奔。”司罕说完就挂了电话。
就顾问骞刚刚那凶狠样,谁杀谁还说不准呢,先前在悍马上的生死时速,已经让司罕领会了这个人的疯狂。顾问骞疯起来什么都不会管,但他是个警察,若是因私杀了人,就没有回头路了。司罕也跑进了两人消失的那扇白色小门。
一分钟后,姜河赶到时,一眼就看到了司罕留在地上的记号。那是一个箭头,他不知何时打碎了几个培养皿,倒出了里面的发光菌群,摆出了一个箭头,指向那扇不显眼的小门。
比起广场上的大型发光培养缸,那些菌群发着微弱的光,合在一起也不太起眼。但这个箭头指明的方向,提供给警方的价值,却让它有一种萤火可比星光的架势——安静、微弱、执着。
被挂掉电话,几次都打不通,姜河气得差点摔手机。一个比一个不听指挥,都他妈乱来!他飞速带人闯进了红日,在门口遇到了似乎等候多时的樊秋水。樊秋水二话不说,直接带他们走过红日里复杂的地形,来到地下室的黑门前,那里正站着周焦。
顾问骞追着徐奔进了小门后,发现里面是类似档案室的地方,小房间非常多,位置错综复杂,和红日很像。徐奔借着地形优势逃遁,和顾问骞拉开了距离。顾问骞唯恐这里还有另外的出口,追得很紧。
没一会儿,徐奔跑进了一个稍大的空间,里面装饰得像是一个小型教堂,在中央供奉的位置上,有一对巨大的手形白玉雕塑。那对手形白玉雕塑,相互靠拢,向上微合,是捧着什么的姿态,有种神圣感。
这双白玉手托着的,并不是一般教堂里供奉的神明雕像,而是一艘船,模型船。船身大约两米长,造型简单,有些简陋,木头做的,有损坏变形的部分,色泽劣质,有些地方是腐烂的,像一艘被打捞起来的陈年破船,随便起个浪就能散架,和底下托着它的白玉手的上好质地形成鲜明反差——这双白玉手“供奉”着一艘破烂船。
顾问骞看到那艘船时,瞳孔骤缩,广播里的惨叫声强行将他的记忆扯出来鞭笞。他死都忘不了这艘船。他不再追了。徐奔正拼命奔向这艘船,好像那里就是逃生出口。
“嘭”的一声枪响,近在咫尺。
徐奔还未反应过来是哪里的枪声,就看到供奉台上的模型船震动了一下,顷刻间散架,从白玉手上破裂开来,流沙一般撒到了地上。那双白玉手此刻真的像是托了些垃圾,托了一场空。
徐奔猛地回头,只见顾问骞举着枪,在距离他十多米远的门口站着。他不敢再动,那枪口已经转向了他,黑洞洞的口子,刚开了枪,还冒着些硝烟。他清楚,他举枪的速度,绝对快不过顾问骞开这一枪。
显然,刚刚打模型船的那一枪,是在威胁他。但徐奔并不紧张,甚至还笑了一下:“你现在不是警察,没有持枪证,你打不了我。”徐奔这话表明了,他果然知道顾问骞的身份。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在自己和司罕来红日之前就知道吗?
“赌吗?”顾问骞表情不变,“赌你会不会变成那艘破船。”
徐奔一顿,随即大笑,挑衅之意尽显。他阴阳怪气道:“你不敢的,那时候给你机会你都没开枪,不是吗?你当时只要打死一个,就能救另外四个了,是你选择送他们都去死的,像你这种人,脑子里只有规矩,你不敢的。”
司罕赶到的时候,听到的就是这句话。先前跑到一半听到枪声,他还急了,以为开打了,就是那枪声让他找到了这里。司罕不由得把脚步放轻了,他不敢上前,不敢发出大的动静,生怕一个喘息都会刺激顾问骞。
顾问骞右手笔直地举着枪,随时会开枪,又或者,他在脑子里已经开枪一万次了。从司罕的位置只能看清顾问骞一半的脸,这一半是不朽的阿喀琉斯,而在黑暗中的另一半,是他正浸在冥河里,被烧去的凡人之躯。再看一眼,司罕又觉得反了,自己看到的那一半,才在冥河里。
徐奔在刺激顾问骞开枪。他要毁了顾问骞。
而顾问骞的神情,让司罕觉得自己回到了悍马的副驾驶座上。
核裂变能停止吗?能,插入控制棒,吸收中子,切断链式反应即可。但司罕不是硼,不是镉,他做不了这个控制棒。他在这个瞬间甚至有些后悔,后悔没把悍马上的车载系统录下来,放给此刻的顾问骞听。能阻止顾问骞的,只有那个叫安琪的系统。
广播里的录音又重复到惨叫声了,和徐奔的笑声交相融合,刺激得人头皮发麻。
即使知道没用,司罕还是开口了,他轻轻地唤了一句:“顾问骞。”话音刚落,枪声响起,顾问骞开了两枪,徐奔闷哼倒地。那两枪像是在回敬广播录音里的两枪,四声枪响重合的时候,仿佛有回声。这两枪,跨过时光,在这一刻还了回去。
顾问骞朝倒地的徐奔走去。到了这一刻,徐奔才流露出恐惧,拖着身体想往后爬,但被一脚踩住了。顾问骞的脚踩在他中枪的地方,徐奔的惨叫响彻地底,比广播录音里的叫声还大。
司罕在原地呆滞了很久,才缓步跟上前。顾问骞开枪的时机,是在听到自己喊了他之后,那一瞬间,司罕都觉得那两枪是朝自己开的,徐奔的中枪声是从自己身体里发出来的。
“你跟Goat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会有那段录音?”顾问骞踩着徐奔,枪口对着他的一根手指,好像他不回答,就要开枪崩掉一根手指。
徐奔面露痛苦,冷汗直冒,他已经不敢笃定顾问骞不会这么做了,这是个疯的。但他依然强撑着,没开口。下一秒,腿上被踩着的伤口传来剧痛,徐奔痛得叫不出声来,耳边是那人似乎失去耐心的声音:“为什么那段过程会被录下来?”
最初意识到那段录音是什么时,顾问骞诧异的不是那反反复复出现在梦里,无比熟悉的经历本身,而是这段经历为什么被录下来了,他们是怎么被窃听的?若不是今天听到了,他到死都不会知道,那时他们居然在被全程录音。所以他们以死相搏,命悬一线的那段逃亡,是在被人观赏吗?冒出这样的念头时,顾问骞几乎肝胆俱裂。
徐奔还是没开口,他偷偷地抬手,想用手中的枪自杀,但被顾问骞发现,直接拧断了胳膊。徐奔又一次惨叫,面色煞白。
“老实交代,你是怎么知道这段过程的,你当时在现场?”顾问骞的语气阴森至极。
徐奔整个人大汗淋漓,已经痛得快抽搐了,但听到这句,居然强撑着笑了出来,扬起脸点头,凑近顾问骞,抽着气道:“不只我知道,所有人都知道,顾问骞,你挺上镜的。”
这话如雷霆之击,所以是他猜的那样吗?Goat把他们的经历录下来做成了片子,抑或当时就在实时观赏?什么时候开始录的?只有他们逃亡那段,还是他们一开始就踏入这些人的频道了?各种荒唐的念头如地鼠一样钻出来,顾问骞不断气血上涌,万念最后都归于一个斩钉截铁的认知——做得出来,Goat确实做得出来。
顾问骞的表情取悦了徐奔,徐奔抽着气笑道:“你不知道吧,你现在站在人群里,就是个活靶子啊。”
又是一击。
原来他的长相早就被Goat公开了,所有成员都知道他长什么样。顾问骞这两年自以为在伪装身份追查Goat,却只是个招摇的笑话,是把自己插在旗上高高举起,喊着敌人来射杀自己。
司罕站在边上,一言不发,只是盯着顾问骞,怕他又动手。听徐奔一句又一句地扎进阿喀琉斯之踵,司罕算是明白了,这人逃回来,根本不是为了摧毁或带走什么东西,就是为了引顾问骞来,折磨他,这会儿还在刺激他,似乎非要顾问骞亲手杀了自己才算完。
看到现在,司罕觉得徐奔和顾问骞没那么大的仇,他这样做必然是被授意的,被谁授意了?
Goat。是Goat要折磨顾问骞。
广播里的录音开始新一遍的重播了,气氛险恶,徐奔似乎已经给自己找好死地了,他朝着供奉台上的白玉手看去,像是打算把留在人间的最后一眼,给他的神。
顾问骞却放开了徐奔,缓缓站起身。司罕这才发现,顾问骞浑身都是湿的,大汗淋漓,像从海里捞上来的。
起身后,顾问骞没再管徐奔,也没处理情绪,而是先做了个无关的举动。他举起枪,拆了弹夹,取出里面的一颗子弹,然后拿起司罕的手,塞进他的掌心。
“9毫米橡皮弹,打不死人。”
司罕怔住了。他这才低头观察起来,发现徐奔身上没有血迹,也没有中弹的痕迹,顾问骞的两枪橡皮弹,打在徐奔的两只脚腕上,是用来限制行动的,只是痛了点,除了为防止其自杀搞脱臼的手臂,徐奔身上甚至没有可见的伤口。
顾问骞这把枪就是虚张声势的,他第一枪是故意把那艘模型船打崩的。而徐奔被唬住了。
司罕盯了这颗橡皮弹很久,仿佛看到了什么新大陆。顾问骞可以不解释的,或者可以更晚解释。但他在这一刻就解释了。司罕想问他,是不是在悍马上,即使没有安琪的提醒,他也会减速。但司罕什么都没问,只是轻轻把这颗橡皮弹攥在手心,放进了口袋里。
外面响起脚步声,姜河带着人下来了,一起来的还有樊秋水和周焦。
姜河看到地上的徐奔时,面色骤变,几步上前,仔细查看过徐奔的身体情况后,才松了口气,如临大敌的表情退去了。
徐奔的枪被缴了,警员对他搜身,防止有其他武器,却搜出来一支黄褐色的迷你手电筒。这立刻吸引了姜河等几人的注意,但姜河没表现出来什么,让警员提交了所有搜出来的证物后,就让人把徐奔带走了。
待警员离开后,姜河才急忙从口袋里拿出之前从李怀儒那里搜来的那支迷你手电筒,和徐奔这支颜色一模一样。他们找了这么久的手电筒,在短短几天内居然接连出现了两支,这太不寻常了,令人在亢奋的同时,又不免胆寒。他们确实在接近Goat。教堂里供奉的那艘破船,以及徐奔的手电筒,都在明示着,他们找到Goat的窝点了。
顾问骞看着那支手电筒,没言语,他还没把司罕也有一支不同颜色的手电筒的事告诉姜河。
姜河远离了人群,轻声道:“加上你那支,总共三支了,但是有两种颜色,这你怎么看?”
顾问骞沉默片刻,道:“颜色可能代表等级。”
“等级?”姜河愣了一下,“你是觉得还存在其他颜色的手电筒吗?”
姜河咂摸了一下,他拿到李怀儒那支后,只猜测过颜色可能是用于分类,认为不同颜色的手电筒代表组织中的不同工种,但毕竟只有顾问骞去过Goat的老巢,对他们的组织模式更了解。
“是合理猜测,”姜河点头道,“如果颜色代表他们在组织中的地位,从目前收到的三支来看,黄褐色的有两支,比青灰色的多,从概率上来说,青灰色的等级可能更高一点。李怀儒和徐奔确实不像Goat的高层,他们是被放弃的那一类。但这只是推测,得收集更多手电筒才行。”
顾问骞“嗯”了一声,暗暗瞟向了远处正在和周焦说话的司罕。他那支粉色的和自己这支青灰色的,哪支等级更高呢?
樊秋水在辅助警员分辨地下广场的物资。他在红日工作了几年,从来不知道地下有个这么庞大的空间。徐奔被警局传唤前,就遣散了患者,把红日关掉了,但樊秋水长了个心眼,没离开,就躲在红日里,果然等到了徐奔去而复返,后面还跟着顾问骞和司罕,三人都很匆忙的样子。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正要跟过去,却在门口发现了探头探脑的周焦,这小孩显然也是在红日蹲守,看到三人进来后跟进来的。但他们没下去,周焦拦住了他,说最好在门口等着,一会儿给人带路。
“给谁带路?”
周焦把平板递给樊秋水,上面是个大型的实时路况系统,他把几条移动交会的路线指给樊秋水,道:“徐奔应该是逃了,现在交警在追捕他,警察应该很快会到这里。”
樊秋水明白了,顾问骞和司罕显然是先追到了,周焦让他在门口等着给后来的警察带路,节省时间。毕竟要在红日这个弯弯绕绕的空间直接找到黑门,也不容易,而仅靠他们两个人追着下去,其实意义不大。
他再次认真看了眼这个不到他胸口的倒三角眼小孩。这小孩仅凭一个交通路况系统就猜到了情况。他是怎么获取警车定位的?这个路况系统是公开的吗?他真的只有十七岁?冷静睿智得可怕。想想自己十七岁的时候,还是个刚刚重获新生的菜鸟。
没过多久,两人果然等到了姜河,带路之后,姜河本来要把他俩拦在黑门之外,但周焦说了一句话,就让姜河对他们放行了,他说:“你们可能会用到我。”
姜河沉默了两秒,考虑到下面的情况确实可能会有需要网侦的地方。樊秋水也见缝插针地来了一句:“我是这里的员工,熟悉地形。”
等下去后,樊秋水就发现话说满了,别说熟悉了,地下广场他见都没见过。但地下广场的复杂布局和红日有种奇特的血缘感,像一脉上的两朵并蒂莲,只是地下广场更大,绽放得更繁盛,樊秋水还是靠着对相似通路的直觉、司罕摆的那个菌群箭头,以及枪声,成功在档案室找到了这个小教堂。
此时他跟着警员搜查辨认,在档案室的一个隔间里,发现了找了许久的录像带,满满一柜子。这些是徐奔私录坦白局的关键证据,果然被藏在地下。
警员找到了地下广场的电闸,把灯全打开了,广场里凌乱复杂的各种设备清晰地映入眼里,警员们都稍有怔愣。他们这是缴获了一个大型地下工厂,他们还记得刚下来时看到这么多培养缸的震撼。
顾问骞厉声道:“查,查这几天在红日停留的大型货车、垃圾车,以及分批次出入的小货车。他把东西转移过了,这些是填进来给我们看的,这个培养缸那么大,不可能是用来装一只羊的。”
姜河顺着顾问骞的目光看去,中央那个足有两人高的培养缸里面那只泡涨的羊,就像一个发育不良的胚胎被移植进了过大的母体,很不协调。
如果不是用来装羊的,那是用来装什么的?姜河的面色也严肃起来。“所有房间、暗格都搜仔细,看有没有人被关在这儿,有必要的话,直接用红外热像仪。”
从红日消失的那六个女性患者,以及生活在地下的那个女孩红日,都还没找到,这个地下广场这么大,地形复杂,难免让人怀疑是个藏人的地方。
不一会儿,单兵手台里响起警员的呼叫,说在教堂后面,找到了一个上锁的小房间,周焦刚刚把门锁破解了。几人立刻赶过去,司罕和周焦已经进屋子了。顾问骞刚踏进去,就给了姜河一个眼神,姜河立刻遣散了附近的警员。
这是个女生的房间。随处可见女生的用品、摆设,所有物品都是单个的。是个单人间,住户的年纪应该还小。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那个叫红日的女孩。看来她真的住在地下。空间不大,几人很快就确定了屋子里没人。名叫红日的女孩在哪里?早就被徐奔带走了?
姜河原本觉得那女孩是被关起来的,但根据顾问骞的描述,女孩能自由出入地下工厂,他又打消了女孩被关住的想法,而此时看到这个房间,他又不确定起来。
房间大约五十平方米,装潢很简约,甚至还是石墙,墙面都没粉刷,像是仓促间开辟出来的一个用来住人的小空间。房间还算干净,有人打扫过,但没有窗户,四面都是高墙,狭小空间给人强烈的闭塞感,让人难以想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会自愿一直住在这里。
周焦仰头看天花板,明明很高,跟教堂一样高的顶,但是越高越压抑,好像一个塔尖,里面的人怎么都爬不出去。房间的右上顶,挂着一幅画,画上是一轮鲜艳的红日。住在这里是看不见太阳的,那幅画挂在那里,似乎是房主给自己造了个虚假的红日。
她到底是什么身份?能自由出入地下工厂,却住在这么破的房间里,还不能被放出去。
几人往里走,很快发现桌上的电脑是开着的。顾问骞点开屏幕后,所有人都一愣。电脑屏幕上赫然是他们熟悉的那个洋葱——洋葱游戏!
红日也在玩洋葱游戏!
屏幕上的紫黑色洋葱上写着“立华二中洋葱号”,可当时马冬军被捕,司罕破解了密钥,立华二中的洋葱测试系统早就自动销毁了,为何现在还在红日的电脑上?
顾问骞蹙眉道:“红日的身份查得怎么样了?”
姜河摇头道:“信息太少,不能确定‘红日’是不是本名。找出了三十几个基本信息吻合的人,还在筛。摄像头截图的部分太模糊了,无法做面孔识别,我怀疑她第一次见你时是故意站在门后那个位置,知道摄像头拍不清她。”
“查立华二中。”顾问骞道。
姜河也已经反应过来,立刻打电话,把对红日身份的调查范围缩小到立华二中。
几分钟后,文件传来,电话在同一时刻响起,红日确实是立华二中的学生,红日就是她的本名,她和周焦同龄同届,周焦两年前就辍学了,红日则是五个月前辍学的。文件里有红日的学生档案,那张照片上的女生,赫然就是这个住在地下的女孩。
“五个月前,正是洋葱游戏兴起的那段时间。”一直没说话的司罕开口道。
顾问骞看向周焦道:“所以你觉得她眼熟,你们是同学,你见过她。”
周焦的倒三角眼停在红日的那张学生照上,肯定地摇头道:“不是,我没有在学校见过她,我没去上过学。”
那你是在哪里见的?总不会是在梦里吧。姜河想吐槽一句,他觉得周焦可能是记错了,毕竟同在一个学校,哪怕周焦没去上过学,离得近,路上遇到也有可能。
“所以红日是玩了洋葱游戏,抑郁辍学了,然后被拐到了这里?也说不通啊,那她为什么能自由出入这里?”姜河快速翻着红日的个人资料,“她的家庭关系网里没有徐奔,他们不是亲属关系,也看不出父母辈的交际,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说到这里,姜河突然顿住了,他收到了一条最新的信息。姜河抬头看向顾问骞,在对方并没有回避倾向的目光下,蹙眉道:“红日,本来是被列在仲永计划里的,但因为辍学,被取消资格了。”
顾问骞愣了一下,敛起神色,没表示什么,也没跟另外两个人解释仲永计划。
沉默间,司罕忽然轻拍了一下周焦。“看看红日的洋葱游戏报告。”
周焦立刻坐下,操作电脑,而后道:“没有报告,她没玩洋葱游戏。”
姜河道:“没玩?那她开着洋葱游戏做什么?会不会是玩到中途退出了,所以没报告,和那个叫阮玉桑的女生一样,被公布了信息?”
周焦摇头道:“她没玩,她都没登录。”
众人琢磨间,突然听到司罕道:“你查一下她的后台,还有没有其他学校的洋葱游戏。”
所有人都一愣,看向司罕。这话是什么意思?顾问骞反应过来,面色沉了一分。周焦快速地切入了后台。
令人惊愕的画面出现了,红日的电脑上,不只有立华二中的洋葱号,还有牧羊一中洋葱号、阳光中学洋葱号、申城外国语中学洋葱号、立华女中洋葱号……足足二十个学校的洋葱号。这些洋葱号,此前都已经在全市排查下被销毁了,此刻又都回魂般出现在红日的电脑上。
姜河不由得吸了口冷气。
司罕盯着那些叠起来的网页窗口,紫色洋葱浮浮沉沉,同时摇摆着,像一串咒语。他幽幽道:“红日不是玩家,她就是制造了洋葱游戏的人。”
一时间没人说话,只剩周焦破解算法的键盘敲击声。马冬军离奇死亡后断掉的线索,在红日的案子里接上了,嫌疑人还是个被关在地下的女高中生,这让人一时难以串联起来。司罕印象中那个亵玩人性、幼稚恶劣的洋葱游戏设计者,和红日的形象逐渐重合。
姜河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问:“凭这些网页就能断定吗?她会不会只是登录了这么多学校的洋葱游戏?”
反驳姜河的是周焦,他一言不发,把所有洋葱测试的底层程序掀开了,解剖一样摊在屏幕上,这里就是洋葱测试的服务器原址。
顾问骞道:“这个地下广场那一大面墙上的超级计算机,就是洋葱游戏背后那个庞大的加密服务器?”
之前警方的系统应该就是在跟这个服务器打网络战。
周焦道:“那是高估洋葱游戏了,高性能计算机群更有可能是基因测序用的,挂一个洋葱游戏只是顺便,相当于从一头猪身上拔一根毛,完全不在话下。”
姜河看了眼这孩子,发现他一提到IT相关的事情,嘴就利索得很,看起来也不自闭了,但这狠毒的小模样,还真无法和他那温和谦逊的父亲联系起来。
姜河有点想骂娘,今天接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追查红日的案子时,居然破了断线的洋葱游戏案,惊喜来得让人不太舒服。这不是巧合,是因为他们找到了Goat的地盘,证明了所有事确实是Goat做的。所以购买了马冬军这只羊的人,就是红日吗?
姜河蹙眉道:“她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教唆学生自杀的游戏?她知道马晓明的事?还是只是借了马冬军的壳?”
没人回答。
只有司罕答非所问地对顾问骞道:“我之前就在琢磨,红日互助中心为什么叫红日,红日又为什么要告诉你,她叫红日。”
这个女孩能自由出入这个非法隐藏的地下工厂,还拥有自己的房间,权限自然不低,她不是被关在这儿的,她也不是普通患者,红日的患者并不知道地下有什么,她们都是工具人,只有一无所知的人,才能扮演好工具,她不是。在徐奔被传讯前,她就已经离开了这里,显然,徐奔是被抛弃的,她不是。这个地下广场的入口,那个精神互助中心,和她同名,她实际生活的地方却是这里。她远比徐奔花了更多时间在红日真正的核心。
“红日这个名字,真的是徐奔起的吗?”
司罕望向闭塞房顶的那轮画中红日。“会不会其实,这里的主人,不是徐奔,而是红日?”他们此刻所处的地方,不是徐奔痛苦的精神世界的投射,而是红日的。是她把这个地方建造成了这样。
几人被司罕的说法震了一下,都没说话。
司罕接着道:“徐奔,只是她抛出来的一条狗,就像红日互助中心,只是这个地下工厂抛出来的一只眼。这里的一切,也都是她愿意展示给我们看的,所以电脑是开着的。她大可以在离开前删除洋葱游戏,但她没有。”
小小的石墙房里,沉默在发酵。
姜河沉吟片刻,道:“Goat是个极其成熟的恐怖组织,他们为什么要给一个患病的女高中生这么大的权限?现在只能确定洋葱游戏是在这里被制造的,到底是不是她制造的,还没有定论。徐奔无论论经验还是论资历,都比她靠谱,没道理断定徐奔就是她的手下,你这只是凭空猜测。”
“患病的女高中生。”司罕念了一遍,笑了一下,“姜警官说得对,我确实是凭空猜测……为什么会这么猜,或许是因为我没见过她。”
他看向面前的三人道:“你们都见过她,亲眼或是通过监控,对她有先入为主的印象。一个患病的女高中生,一个生活在幽暗地下的无助者,一个可能和周焦一样的未成年天才。”
他讲到最后一句时,顾问骞瞥了他一眼。
司罕道:“我没有这些印象,只听过对她的描述。徐奔说她是个重症患者,最好别接触,会被污染。我虽然不明白‘会被污染’是什么意思,但徐奔惧怕她。顾问骞对她的描述则是:她认为身上的水流光了,很渴,她的身体是一艘船,叫诺亚方舟。她的精神世界,是宁可流光身体里所有的水,去供养一艘方舟航行的啊。她给我的印象,起码在精神上,是个庞大的存在,我们或许只是她那艘船上的一个小窗口。”
没人再说话。姜河沉默良久,道:“我会把你的说法作为其中一个方向去查。”
这回轮到司罕诧异了,这个姜警官怎么变得好说话了?之前总是对他横眉冷对的,这一下还让人怪不习惯的,他连忙客气了一句:“尽力就行。”
姜河:“……”怎么跟他领导说话似的。
顾问骞冷不丁地对司罕道:“你知道仲永计划。”他们没解释过仲永计划是网罗天才少年的,但司罕刚刚却直接点出了红日和周焦的相似处。
司罕弯了弯眼睛,坦然道:“你们要不去看看仲永计划的伦理审批里,心理健康教育的司法鉴定委员组成员都有谁……啧,它这么快就通过啦。”
顾问骞刚蹙起眉头,就听司罕又补了一句:“哦,我投的是反对票,但我只能投一票,没啥用。”
顾问骞的眉头舒展了。
“我想起来了。”一直没吭声,忙着把红日的电脑翻个底朝天的周焦,突然开口了。
“想起什么?”
“我是在哪里见过这个女生。”
“哪里?”
“在一幅画里。”
姜河问:“画?”
这个答案让他有些诧异,他还以为是这两人都曾被列在仲永计划里,有过什么交集。
顾问骞问:“什么画?”
周焦的倒三角眼显出一种专注:“一幅由AI绘制的画。”他拿出自己的平板,开始找了起来,很快,在相册里翻出一张图片,递给几人看。
姜河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这是什么东西?这张图片太大,为了看清细节,他们上下左右,足足翻了十几秒,才看完了这一整幅令人吃惊的画。
这幅画众人并不陌生,是米开朗琪罗画在西斯廷天主堂祭台后方整面墙壁上的《最后审判》。它太著名了,图片广为流传,哪怕不信教不赏画的人,也都多多少少知道点背景,看过这画。这幅画是米开朗琪罗受教皇之托被迫画成的,承载着艺术剥削和精神与信仰的危机之痛。他把痛苦体现在了画中,选择了“最后审判”这一主题,描绘了基督重生归来后,要审判生者和死者的场景,被他免罪之人能获得永生,而被他判罪之人则永入地狱。
画中有四百多个人物,构图磅礴,细节形象,每个人物都有迥异的神情,米开朗琪罗描绘了一幅末日中人类集体崩溃的悲剧景象。画面有四个层次:最上层是天国的无翼天使,他们簇拥着基督受难时的十字架和耻辱柱,号角宣告着审判开始;画面中央是神态威严的基督,以及他的门徒和殉道圣者们;画面下部是善恶两部分人正受到基督的裁决,左侧的人物升往天国,右侧则是被打入地狱的亡魂;右下角的水面上是地狱的引渡船,地狱中是被大蛇和魔鬼缠绕的罪人。
周焦所展示的AI绘制的画,几乎是临摹了一幅一样的《最后审判》,不同的是,一开始米开朗琪罗画的是全裸的人物,但在他去世后,教皇就命人给所有裸体人物画上了腰布和衣饰,而这个AI把衣饰又去除了,所有人物恢复了全裸的形象,赤条条地面对基督和审判。
这并不是让他们惊愕的地方,令他们惊愕的是,这幅画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同一张脸——红日的脸,她的面孔出现在天使的脸上、基督的脸上、圣母马利亚的脸上、善者的脸上、罪人的脸上、魔鬼的脸上……她的神情随着不同的人物状态变化,形象细致,毫无不协调感,恐惧、震怒、怯懦……这四百多个人物,竟全是红日所扮。
姜河看着都觉得生理不适,再去看手机资料上那张恬静的学生照,他只感到一阵头皮发麻。司罕和顾问骞也都沉默着,面对这样一幅画,没人讲得出话来。
周焦语气平静道:“这是一个受过艺术熏陶的AI画的,它出过不少作品,被作为艺术AI培育。但它所有的画作都是被指定了主题的,当训练者让它自由创作,不再给主题后,这个AI沉寂了很久,没有动静,于一年后,突然交出了这样一幅画,交完它又归于沉寂,不再画画。没人知道画中这张女性的脸是谁,看画的人都以为是这个AI自己创造的一张脸,训练者自己也是这么说的,我也是刚刚才想起来,红日的脸和画中的脸一模一样。”
周焦的解释非但没有解决几人的疑惑,还让疑惑加深了,这个AI是见过红日吗?为什么要这样画?
顾问骞问:“这幅画你是在哪里看到的?什么时候看到的?”
周焦双目微垂,顿了一会儿才道:“三年前,在一个私密的人工智能论坛上。那个论坛已经被封掉了。”
顾问骞的目光从画上移到了周焦的脸上,沉默片刻后道:“你想跟着我们?”
几人不明白他为什么在这时突然说这个。周焦点了点头。
“那有一点要注意,不要对我说谎。”
司罕和姜河一愣,目光都跟雷达似的把周焦上下扫了个遍。周焦说谎了?哪一句?周焦依然没什么表情,和顾问骞对视着,而后移开目光,半晌才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
樊秋水进来了,看到几人都围在一起,愣了一下道:“你们还没弄完?外面都搜出一堆东西了。”
“你过来。”顾问骞道。
樊秋水走过去,也看到了那幅画,他的反应倒不大,只是蹙眉道:“怎么都画成了一张脸,这盗版也太离谱了……让女性也拥有阳具,是后现代画风?”樊秋水小时候是练国画的,虽然技艺荒废多年,对国内外名作的赏析还是记得些。
“你认识她吗?”
樊秋水一愣,一时没分清是不是玩笑:“画出来的人,我怎么会认识?”
顾问骞道:“她就是在红日地下的那个女生,你真的一次都没见过她?”
樊秋水吃惊地又看了看画,摇头道:“没见过,要不是你说,我都不知道地下有人,只有小空找我问过一次,说住在黑门后的姐姐在哪里,我只当他是童言无忌,在讲鬼故事。”
姜河蹙眉,红日藏得很深,樊秋水这样的老员工都从来没见过她。
顾问骞却不再说话,陷入了沉思,姜河以为他还在为那幅画烦心,想说点什么,却听一旁的司罕悠悠道:“那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樊秋水在这里几年,都没见过她一次,顾问骞来的第一天,就见到了红日,她是主动被他看到的。”
姜河一愣,才反应过来这件事。顾问骞没什么表情,显然他也在想这件事。
司罕道:“如果她没主动现身,我们还没那么快查到这个地下工厂吧?她为什么要冒着被发现的风险,让顾问骞看见?”
姜河越听眉头皱得越深,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司罕笑道:“你别紧张,就事论事而已,我肯定不是在怀疑你那好队长,但他是怎么被盯上的,总得注意一下吧。”
姜河面色变得难看,不再说话。
顾问骞道:“我第一次和她面对面,她说的话也很奇怪。她说,她不是在看我,她是在照镜子。”
“照镜子?”司罕眯起眼睛。
“嗯。”
樊秋水见所有人都在沉思,便独自在屋子里逛了起来。这是他的职业病,总想收拾病房,他进来后刚看了一眼,就觉得这房间像个病房。
他走到床边,想整理一下床铺,在靠近墙边时,却突然停住了。
“你们过来看,这里刻了一行小字。”
其他四人被樊秋水的话吸引,都走到了床边,凑近看了好一会儿,才在床沿发现了那一行袖珍的字,像是用指甲刻的,墙是石墙,指甲随便划两道就能留下印子,那行字虽然不显眼,但细看是能看清楚的。
红日:夏娃二号。
姜河问:“夏娃二号?是什么?”
樊秋水道:“像个代称。”
“这个‘红日’指的是人,还是那个互助中心?”如果指的是人,这行字的意思是那个叫红日的女生是夏娃二号?
“会不会是Goat的成员称号?”
没人能回答姜河,疑问一个接着一个。为什么这行字被留在这里,谁留的,红日?夏娃二号是什么?为什么是二号,是还有夏娃一号吗?姜河觉得头痛,今天虽然查到了Goat的一个窝点,但获得的信息却让谜团变得更深了,Goat越发扑朔迷离。
司罕看了一会儿,却站起身,重新拿起周焦的平板电脑。他指着画上中央的一点,缓缓道:“《最后审判》里,基督和圣母马利亚的左下方这两个人,左手拿梯子的男人,被普遍认为是亚当,而他身后那个披着头巾的女人,被认为是夏娃。”此刻画中的夏娃,面容宁静,望着画外,正是红日的脸。
对地下广场的搜查持续了三天,又找到了几个有过女性居住痕迹的小屋。但和红日那间房随性的样子截然不同,这些小屋更规范化,像是从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但没在里面找到人。根据从屋子里采集到的毛发的检测结果,可以确定,那六个从红日互助中心相继消失的女性患者,曾经就住在这些规范化的小屋里。里面的东西明显被清理过,看不出到底把人关着做什么,现在又把她们转移到了哪里。
姜河比较急,尽管人已经失踪几年了,但立案是在这次的红日事件里。很快就要到她们失踪四年,宣告死亡的时效期了,得在那之前找到人。而且也不确定她们是否还活着,从地下广场被转移的时间是多久以前,如果是近期,就还在紧急救援的黄金时间范围内,超过这个时间范围,她们死亡的概率会变大。
“那几个小屋里没有鲁米诺反应,没有明显的被虐待痕迹,徐奔把她们关在这里到底是要做什么?”姜河来回翻看这六个女性患者的资料,试图找到破局的共同点,“应该说,Goat要用她们做什么?”
司罕道:“这是个大型生物实验室,这些女性患者应该是实验体。”
“做什么实验?”姜河不是没想过这个可能。
顾问骞看着广场中央的培养缸里那只泡涨的羊,开口道:“她们可能是孕母。”
姜河顿了一下,只选择女性作为实验体,这个可能性很大,但他质疑道:“这六个女性都是精神病患者,徐奔为什么要挑她们做孕母?他创立红日互助中心,必然和诱拐人口的目的有关,他为什么不创立一个健康人群的女性互助组?只是因为易得性吗?”
司罕的眼神在红白光下显得晦暗:“如果,存在这样一个实验,需要用到精神病患者的生育功能呢?”
姜河一愣,思考了半晌,蹙眉道:“红日互助中心筛选对象时有年龄偏好,找的都是三十岁到四十岁的女性,真如你所说,要用到精神病患者的生育功能,他为什么不挑更年轻、更具备生育优势的女性患者呢?”
司罕沉默片刻,道:“你按照他们的思路去想,高龄产妇,孕期环境不良,容易导致胚胎发育异常,精神病患者,具备精神病的遗传性,或遗传易感因子。两者叠加,这个实验想要的可能是缺陷儿,精神上的缺陷儿。”
两个警察都愣了。姜河张了张嘴,半天才憋出一句:“你是说,Goat在大批制造先天性精神缺陷儿?他们为什么不直接网罗已经存在的——比如小空,就在眼皮底下——而要绕这么大个圈子,从胚胎去制造,为什么?”
司罕耸肩道:“谁知道呢,我又不是Goat肚子里的蛔虫。”
姜河被这句话堵了回来,心里不太是滋味,好像临门一脚被人踹回了老家,这只笑面虎总有这种管杀不管埋的本事。他转头去看顾问骞,见顾问骞没有反驳的意思,这是认可司罕的推测了?
久不出声的顾问骞开口道:“去排查其他生物工厂,特别是隐蔽非法的。Goat真要这么做,避不开大型基地,她们可能被转移到了那里。”
停顿了一下,他又补了一句:“尤其关注一下造在海边的生物工厂。”